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造富運動,無論從人數上,還是從財富總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一兩百年的歷程。
父輩的奢侈品變成中國人的必需品
經濟發展關係到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夠提高。中國時評人杜君立認為,在全球化的 “大鍋飯” 中,勤勞的中國通過供養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國得到了鈔票或者債券。
如果對人類歷史進行簡單歸納,大體可以分為植物時代和礦物時代。在礦物時代之前的幾千年裡,人類始終掙扎在溫飽邊緣,有限的植物資源使戰爭和飢荒周而復始的出現,這就是所謂“馬爾薩斯陷阱”。但礦物時代顛覆了貧窮的傳統。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一個前現代的貧窮中國就變成一個後現代的富裕中國,父輩們的奢侈品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必需品。這無疑是一場財富的革命。
植物時代也可以說是農業時代,人類幾乎所有的財富和必需品都無一例外地來自植物。從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時代,但直到 200 年後的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時代,一切物質幾乎都依賴土地上植物的生長:食物、木材、棉花、燃料等,為了保證每個人的“糊口”問題,中國所有的土地都被種上了莊稼(“以糧為綱”),實在不能耕種的土地也種上了各種可用作建材或燃料的植物。對一個將近 10 億人口的中國來說,極其有限的植物生產只能使貧窮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當中國融入全球化經濟大潮時,中國很快就走出了持續數千年的植物時代,全面進入礦物時代。這一過程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上一輩人還是以步行來移動,這一輩人就已經通過汽車和飛機來移動。
礦物時代最典型的物質就是石油、煤炭和鋼鐵。 30 年時間,中國的石油、煤炭和鋼鐵消耗翻了數十倍,徹底改寫了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的面貌。對當代中國人來說,食物、衣物、建築、家具、設備、燃料等各種生活必需品幾乎都來自礦物質,而不再是來自植物。對一個當代人來說,他完全生活在一個礦石物質裡:化肥催生的糧食、鋼筋水泥的房屋、鋼鐵海綿的汽車、塑鋼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纖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等。廉價的礦物時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質過剩,自動化機器的普遍使用幾乎消滅了勞動與工作,人成為一種坐享其成的 “消費動物”。
如果說植物時代人們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麼進入礦物時代後,人們則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 “我們不只是繼承了祖輩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兒孫的地球。”經歷數百億年才形成的地礦資源被當代人一朝之間神奇地打開了。
不可思議的暴富幾乎前所未有
從歷史看,中國當下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議,甚至連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們視為平常的物質生活。更不可思議的是,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 30 年間。 30 年前,人們最奢侈的理想還是吃上一口飽飯、穿上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有一間不漏雨的房子。30 年後,人們將滿桌的飯菜倒進垃圾桶,衣櫃裡堆滿從未穿過的新衣,無人居住的新房隨處可見。如果用數據來說,1979 年,佔中國人口 80% 以上的農民群體人均存款不足 10 元人民幣,而安徽鳳陽縣每個農民平均存款只有 0.5 元;2009 年,中國成為全球儲蓄最高的國家,人均存款超過一萬元人民幣,而黑領雲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將近 10 萬。雖然有極其可怕的通貨膨脹和貧富差距,但 30 年成長了 1000 倍,這是一個無可質疑的事實。從1979年到 2009 年,中國 GDP 成長了將近 100 倍,人民幣總量增加了 700 多倍。這種高達百倍的物質激增只能用 “暴富” 來形容。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化肥、鋼材、水泥的生產國和消費國。過去 20 年中,中國的鋼鐵、水泥、塑料和化學纖維產量分別提高了 5 倍、10 倍、19 倍和 30 倍。作為礦物時代的標誌物,中國的汽車數量在不到 30 年裡成長了 1 萬倍。 1978 年,中國千人汽車擁有量名列世界倒數第一;1985 年中國汽車保有量不足 2 萬輛,如今汽車總數超過 2 億輛,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憑心而論,這種 “暴富” 是 “技術” 的結果,因為中國掘開了地球。雖然比起西方國家來,中國仍然是一個 “窮國”,但這中國人的暴富並不矛盾。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的中國一樣有這麼多一夜暴富的 “暴發戶”,整個中國社會都瀰漫著一種 “小人乍富” 的瘋狂與迷茫。不可忽略的是,在這一輪輪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著混沌無序的社會環境,撐鼓了自己的腰包。
不同年代暴富的手段大不相同
1980 年代,當時暴發戶主要是 “倒爺”(靠轉手買賣的投機份子),靠特權批出內部低價商品,轉手到市場高價賣出,小到肥皂,中到電視,大到鋼鐵汽車。其巔峰是 1989 年牟其中從俄羅斯倒來一架圖 154 飛機,轉手賣給了四川航空,這讓他成為中國最大的 “倒爺”,原因在於訊息的不對稱,因為他知道俄羅斯飛機賣不出去,卻急需輕工業產品。據他後來自稱從中賺了 8,000 萬到 1 億人民幣。而 “官倒” 通過 “批條子” 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是上個世紀 80 年代腐敗的主要形式。
上個世紀開始的中國國營企業改制潮中,一大批國營企業員工下崗,而也有一批人因此富起來了。尤其是當年頗具爭議的民營企業入股和 MBO 模式,非常容易出現暗箱操作、導致國資賤賣。
1990 年 A 股開啟後,坐莊操縱盛行,大批億萬富豪湧現,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 “德隆系” 表現為一種現象,即一個龐大的金融控股集團,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價無一例外地巨幅上漲。有點評稱,德隆內外兼修全面控制 “老三股” 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種違規手法—內部交易、市場操縱等於一身的模式,唐萬新做到了極致。不過,在 21 世紀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 股票大多數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產入獄。如廈門遠華案的賴昌星,規模上百億,將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後逃到加拿大也難躲牢獄之災。據悉,上個世紀潮汕等沿海地區一直有一些 “走私致富” 的神話。譬如,當時潮汕形成一個個採購、運輸、銷售、融資等職能分工明確的集團。湛江一些走私團伙也從家族式管理走向社會化,與汕頭、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結,規模化作業。在這些地區,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當年的金融市場違規操作,讓很多人渾水摸魚,成了富豪。據說,當年的 “327 國債” 事件至少讓四個人完成了原始積累,或者發了大財:當時 28 歲的魏東,29 歲的袁寶璟,34 歲的周正毅以及 30 歲的劉漢。在 327 國債事件中,有消息稱魏東個人賺了約 2 個億的人民幣,隨後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藥業和國金證券等,成為資本市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在 2008 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樓身亡,年僅 41 歲,身後留下了巨大的謎團。
進入新世紀,國內百億級、千億級富豪層出不窮,這來自於三個歷史性的機遇。
一是 “世界工廠”。國際資本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結合,西方市場向中國打開,很多民營製造業老闆抓住這個機遇,由此身家十倍成長,成為億萬富豪。
二是 “房地產市場化和礦產私有化”。這個財富再分配造就了一個空前的富豪集群。中國億萬富豪中幾乎近一半是房產商,身家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經超過 1,000 億人民幣。
三是 “人民幣升值引發國際熱錢投機中國”,助推了 2007 年的超級 A 股大泡沫頂峰、2011 年創業板造富頂峰、2013 年樓市頂峰。
當然,造富運動的渠道還有很多,如大型連鎖式商業企業、煤炭、礦山等行業。中國式的造富運動,從八十年代初的 “萬元戶” 到現在的億萬富翁,前後才三十年。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已高達數兆,億萬富翁已多達千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擠進全球富豪榜中。
暴富並沒有讓大家感到幸福安全
在慾望和金錢面前,人的想像力總顯得如此貧乏。雖然中國所擁有的物質財富是 30 年前父輩們的幾十倍上百倍,但中國的滿足感和幸福感並沒有提高太多。
全球知名財經媒體《富比世》中文版聯合宜信財富發布最新調研成果《2015 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富白皮書》報告顯示,2014 年底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總額約 106.2 兆人民幣,年成長 12.8%,主要由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性資產增長所帶動。估計 2015 年底,中國私人可投資資產總額將達到 114.5 兆人民幣,中國大眾富裕階層的人數到 2015 年底人數可能達到 1,528 萬人。參考國際通行標準,富比世中文版定義的大眾富裕階層是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 60 萬人民幣至 600 萬人民幣之間(約 10 萬美元到 100 萬美元)的中國中產階級群體。其中,個人可投資資產包括個人持有的流動性資產,如現金、存款、股票、基金、債券、保險及其他金融性理財產品,以及個人持有的投資性房產等。
有媒體稱,繼上世紀 70 年代的勞工移民潮以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技術、留學移民潮之後,現下的中國迎來了第三波大規模的移民潮,社會精英和新富階層是 “出走” 的主力軍,主要手段是境外投資,因此又被稱為是移資潮。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律科學博士胡天龍認為,中國富人階層在強大物質基礎上完成移民基於三大動因:關注子女教育、保值增值需要、追求生活質量。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是富豪海外投資的首因。胡潤此前統計稱,85% 的千萬富豪為子女選擇國際化教育,其中中學留學的比例高達 56%。這一趨勢帶動了海外房地產市場。
基於方便移民、以房養學、較低價格和永久產權等考慮,中國富豪紛紛選擇在海外置產,其中擁有海外資產的已達 1/3,在尚沒有海外資產的富豪中,也有將近 30% 的人在未來 3 年有進行海外投資的計劃。為迎合這一趨勢,不少國家為來自中國的財富開通了綠道,各國對華簽證政策放寬的消息不斷傳出。
子女教育考量以外,43% 的富翁把保障財富安全作為投資移民考慮的第二大因素。 “由於目前資本市場處於低潮期,國內資本流動出現限制、跨區域投資政策不透明等因素,持有大量資產的企業主在投資方向和目標上出現偏差和真空,難以維持此前相對理想的發展速度和企業收益,因此希望從國外尋求途徑,實現資產的增值。”胡天龍說。
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市場經營較為完善,國內私營和個體經營者希望通過移民方式到商業競爭更為規範的環境中取得融資便利等條件。獲得一些發達國家的居民身份,也確實更容易在世界各國進行商務旅行,有利於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類似例子在國外稀鬆平常,有歐洲商人為了投資方便而獲取美國綠卡,也有美國中小企業者為了發展,轉換身份到澳洲、拉美國家等進行投資。另外,人民幣與國際貨幣匯差對成本和利潤的影響,促使高資產群體轉移部分資產以保值。
富豪的不安全感還出於對 “原罪” 和 “仇富” 的擔憂。胡天龍認為,部分個體經營者在獲取財富的初始階段,利用了社會制度轉型期的便利、道德體系轉換時出現的漏洞,所獲得的財富處於 “灰色狀態”,他們擔心國家會對擁有非法私產的個人展開 “秋後算賬”,便傾向於把財富轉移到私人財產保護體系更完善的國家,以分散和規避風險。另外,中國部分人對富人的仇視,使得富豪對未來的變化產生不確定感,從而到國外尋求安定的環境。尋求更高的生活品質、可多生子女等也是投資移民的實際考慮。胡天龍說,目前中國處於經濟社會、人文發展的敏感階段,具有經濟實力的人群更希望在法律制度健全的環境下尋求更高的生活品質,比如享受清潔的空氣、放心的食品、健全的社保體系、完善的公共服務、便捷的旅遊出行等,而這些生活條件在中國有錢也未必買得到。
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慾求卻永無止境。大量生產帶來的豐裕與過剩已經成為礦物時代的基本狀態,一方面人們從滿足需要走向滿足慾望,炫耀和囤積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另一方面,產能過剩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和失業危機。財富在放大富人榮譽感的同時,也加深了窮人的罪惡感,從而破壞人與人之間的認同與信任,導致整個社會的幸福感缺乏。
在活著的問題解決之後,活法就成為最大的難題。你幸福嗎?你缺什麼?這是中國當下最流行的 “慰問”。在 “拆哪” 面前,人類延續數千年的物質傳承習慣已經崩潰,一次性成為礦物時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
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面對歷史豐厚的饋贈,我們只是此時此刻的即時存在。在一個浮躁淺薄的暴富時代,中國不僅失去了關於歷史的自省與謙卑,也失去了關於未來的擔當與想像。
中國的很多富人仍沉醉在財富神話中,貪婪而傲慢,很少人意識到未來危機的嚴峻性,他們雖在中國國內是逞威的狼,然而現正面臨全球虎豹的圍獵。即便有所警覺,也大多數缺乏應對突圍的能力。如今中國億萬富豪中近一半是房產商,但中國房市泡沫總有一天會破滅,當下房市下跌已經讓很多房地產商資金鍊斷裂,甚至跑路。在上一波造富潮中,“世界工廠” 成為一大推手。很多民營製造業老闆抓住這個機遇,由此身家十倍成長,成為億萬富豪。但如今,中國廉價勞動力優勢不再,大面積的低階製造產業無法升級轉型,等待他們的可能將是艱難的未來。以前美元貶值熱錢湧入曾對中國造富錦上添花,而今美元復興熱錢外流,難免對中國落井下石。
此外,富二代接班也已經成為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最大的心頭痛。譬如此前媒體報導的山西海鑫集團董事長李兆會,其接班的十年,也是家族實業盛極而衰的十年。富二代如果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很難在未來的變局中守業。
中華元智庫創辦人張庭賓警告稱,未來 3 年內 80% 的中國富人將返貧,首當其衝的是礦產、房地產和鋼鐵等重污染領域。本質而言,是他們精神太過貧乏,物質太過囂張,當社會遊戲規則改變時,他們缺乏足夠智慧改變自己,因而守不住財富積累。
正如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的盛世危言:“我們擁有的財富史無前例,我們從中所得之少也史無前例。人們正在過剩的豐裕中死去!”。
《雪球》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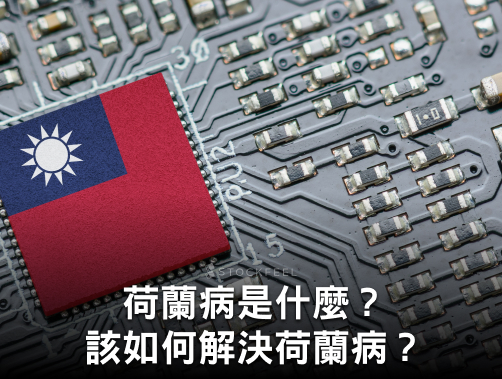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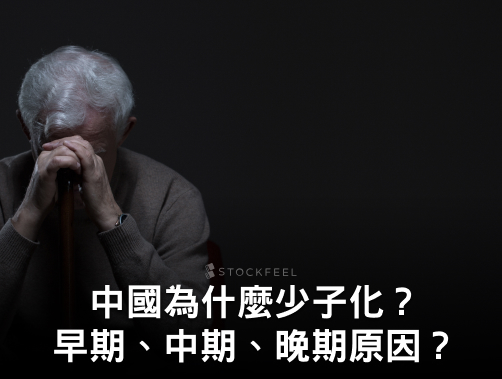



從日本泡沫化的罪與罰-看中國的經濟泡沫-_-.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