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芬頓郵報》稱邁克爾·路易斯(Michael Lewis)是“當代卓越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一”,這一點毋庸置疑。他的暢銷書《魔球》(Moneyball)、《攻其不備》(The Blind Side)和《大空頭》(The Big Short)都已經被拍成熱賣電影。在最近的一本書中,路易斯講述了兩位認知心理學家的故事,半個世紀以前他們對偏見和批判性思維的研究在許多領域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抽絲剝繭:改變我們思維的那段友情》(The Undoing Project: The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一書探索了著名認知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之間非凡的友誼,以及由此產生的關於思維工作原理的重要理論,和這一理論如何幫助我們得出更加準確的分析。最近,路易斯也來到了天狼星衛星廣播公司111頻道沃頓商業電臺“沃頓知識線上”節目探討他的新書,並解釋為什麼他的最新項目可以被看作《魔球》中發現的資料分析戰略的前篇。
沃頓知識線上:這本書可以追溯到《魔球》,為什麼會這樣呢?
邁克爾·路易斯:《魔球》跟這本書聯繫在一起挺偶然的。在我看來,《魔球》主要講的是市場是如何誤估人的。故事的主題剛好是棒球運動員,它講的是奧克蘭運動家隊(Oakland A’s)的故事。他們的資源比競爭對手少,所以必須透過不同而且更好的方法來發掘棒球運動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棒球運動員市場沒有效率。有些優秀球員不被賞識,有些能力平平的球員卻被高估。
當他們在奧克蘭處理業務的時候,他們意識到棒球球探犯了系統性的錯誤,他們決定探索和利用這些錯誤。《魔球》出版後,有一位經濟學家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和一位律師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發表了評論。他們說,“邁克爾的故事講得不錯,但他似乎並不瞭解自己的書。”他們說球探思維中存在的偏見是認知偏見,以色列心理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已經發現和討論過了。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兩人的名字,我在想,“天哪,我怎麼會錯過這個?”但是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麼?思維是怎樣進行的?我甚至根本沒有想到有人已經研究過了。
我用了八年時間才完成這本書。在那篇書評之後,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終於想到打電話給丹尼爾·卡尼曼,我說“我想跟你談談這個問題。”當時他就住在伯克利離我不遠的山上。所以我就上山去了,我們喝了咖啡。
接著我們就在山間走起了長長的路。就在那次,我聽到了他和特沃斯基之間的友情故事,然後我意識到《魔球》以及整個這種現象都只是他們研究上的一個分枝,但是這一分枝卻延伸到了行為經濟學領域。它創造了行為經濟學。你發現它對醫藥和法律等等其他領域也有影響。我覺得他們的這段關係,他們兩個人太不可思議了,這段關係就像一場無性的激情熱戀,他們為彼此而欣喜若狂。在這段關係中也有許多波瀾。這也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合作。最後,我終於意識到了這本書應該自成一格。就像《魔球》的前傳那樣。
沃頓知識線上:他們的研究和理論發生在50年前,是嗎?
路易斯:差不多。1969年他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相遇,直到1979、1980和1981年間,他們的關係開始破裂。1981年到1982年,他們那時分別在史丹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阿摩司·特沃斯基最後去了史丹佛大學,丹尼爾·卡尼曼去了普林斯頓大學。
所以他們的研究的確是很久之前做的,都登在晦澀難懂又無趣的心理學期刊上。這項研究本身並不枯燥,但是文章卻冗長乏味,那些文章並不是給心理學領域以外的人看的,除了1974年他們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寫給大眾讀者的文章。那篇文章觸及了所有學科領域裡的讀者,文章裡的內容影響了人們的看法,雖然也用了一段時間。有時候有些觀點的確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生根。
他們向很多人解釋為什麼專家的判斷也會出錯,為什麼你在判斷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專家的直覺判斷本身就存在易謬性。接著資訊革命出現了,然後是電腦革命,資料和演算法生成的成本越來越低,它們可以用於分析和決策,而這些工作以前是由人完成的。那麼奧克蘭運動家隊也會這樣做,對吧?他們嘗試發掘更新更好的方法來收集和分析棒球球員的表現資料。這些運算最後成了他們投資決策的基礎,而不是去問球探,“那個球員怎麼樣?”
沃頓知識線上:但這也是因為奧克蘭運動家隊並沒有那麼多錢去投資。他們必須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現在這一理念已經被許多棒球隊廣泛採用,甚至是那些坐擁數百萬美元的球隊。
路易斯:你再怎麼有錢,也沒理由去做愚蠢的投資。最後紐約洋基隊(Yankees)、波士頓紅襪隊(Red Sox)和芝加哥小熊隊(Chicago Cubs)也想明白了,他們雇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的“弟子”,還有那些認可奧克蘭運動家隊管理方法的人。結果,奧克蘭運動家隊又陷入了困境,因為那些有錢的球隊現在有的不僅僅是錢,還有相同的智力資產。
沃頓知識線上:你說丹尼爾·卡尼曼和阿摩司·特沃斯基是你曾經接觸過的兩個最神奇的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路易斯:從他們嘴裡說出來的每一句話,他們頭腦裡思考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有趣。我知道只要我把他們說的話和他們的行為寫出來,他們身上的特徵就會影響人們的思維。人們就會開始思考,阿摩司·特沃斯基會說什麼,或者丹尼爾·卡尼曼會說什麼?
人們說起他們倆個總是讚不絕口。密西根大學有一位心理學家叫理查·尼斯貝特(Dick Nisbett),他與阿摩司在一起呆了很長時間後設計出了一個單行智力測試。這個測試是:在你見到阿摩司後,你用多長時間才能意識到阿摩司比你聰明,你用的時間越長,說明你越笨。每個認識阿摩司的人都說,“是的,確實是這樣。”他對此並不反感。只是有時候他有些令人氣惱。事實上,他是以色列軍隊中的一名斯巴達武士。他也是一位功勳卓著的戰爭英雄。他有趣、幽默,樣樣都好,他能把你說的話變成他的,而且說得比你有趣多了。
這樣的趣聞軼事太多了。有一次他參加一個聚會,與會的都是一些世界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他們並不知道他是誰。他在那裡出現好像是偶然的。聚會過後,一位剛剛獲得知名物理學獎項的年輕物理學家給聚會的女主人打電話,問“跟我講話的那個物理家是誰?”他說的是阿摩司。女主人說他不是物理家,“他是一個心理學家。”那個人接著說,“不可能啊!他是我見過最聰明的物理學家。”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他有著邏輯學家那樣像鑽石切割刀一樣的思維。他就是能夠看到別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而丹尼爾就像創意的源泉。他是詩人/小說家一類的人,雖然他堅稱自己是個科學家,但他總是有著最讓人眼前一亮的原創洞見和觀點。對他來說,想像力甚至有可能遵循著某種規則,而不是自由流動的事物,你可以研究想像力,把人類的想像力按規則進行分類?然後設計測試來完成分類?這就是他一個下午所做的事情。
我再舉個例子。這絕對是真的,而且非常深刻。他們兩人都跟現實世界的連結非常緊密,他們可不只是坐在教室裡的人。因為他們是以色列人,每六年他們都要出發作戰或被人當成靶子。他們也訓練空軍飛行員和坦克指揮官等。
有一天丹尼爾在訓練空軍指導員,他注意到他們一直在說,“當你在教一個飛行員的時候,表揚沒用,只要批評。”他問“為什麼?”他們說,“當飛行員做的不錯,我們表揚了他們後,下一次他們總是要差一點。而當他們表現得不好,被我們狠狠訓斥後,他們就會做得更好。”丹尼爾說,“這叫均值回歸。你們所看到的只是假象。他們表現出色的時候,通常也只是比一般情況好一點,但是他們的表現有一個中值,下一次他們的表現很可能會產生中值回歸。”
他不僅看到了這一點,而且他還意識到作為老師,我們可能註定一輩子都會覺得批評比表揚更管用,而且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就因為我們看到了人們通常這次表現不好,下次就會好,這次表現好,下次就會不好。
這些話是四五年前我跟他交談的時候他說的。我從當時到現在都在培訓我的孩子們的團隊。丹尼爾的話改變了我的培訓方式。以前我會注意到,當你批評他們的時候的確有用。如果他們表現不好,你批評他們的話,他們的確會做得更好。如果他們表現好,你表揚他們的話,似乎沒什麼作用。但事實上,這都是謬論,這只是一種假象。所以我在培訓的時候做了一個巨大的改變,把表揚和批評的比例變成3:1,來抵消這種趨勢。
丹尼爾·卡尼曼分不清籃球和足球,他對運動根本沒有興趣。他覺得《魔球》能以這種有趣的方式從他的研究中抽離出來挺奇特的。他說的話有時候真的會改變你對做某些事情的看法,而他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有人在做。
沃頓知識線上:阿摩司·特沃斯幾年前去世了。從丹尼爾或者其他人那裡,你得到了多少關於他的資訊?
路易斯:阿摩司死於1996年。在我開始寫這本書之前,我覺得要想讓阿摩司在這本書中起死回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寫這本書還有很多大挑戰,但它們都不算什麼。阿摩司的個性非常鮮明而生動。對那些給已經逝世的人寫傳記的作家來說,他有一個特徵非常有用,那就是他從來沒有做過他不想做的事情,甚至是以最極端的方式。
如果他和他妻子去看電影,他會在五分鐘內做出判斷。如果他覺得這部電影很平庸,他就坐上車回家,坐在沙發上看《希爾街的布魯斯》(Hill Street Blues),然後在電影結束時接妻子回家。他會說,“他們已經拿走了我的錢,難道還想占用我的時間嗎?”
畢業生都聽過阿摩司收到相當多的郵件的故事,每個人都想和阿摩司見面。每個人都想知道他怎麼想。他會翻翻這些郵件,只看看信封,也不打開,就扔進垃圾桶裡。他會打開一封或兩封信,抬頭說,“我有一個原則,他們能為我做什麼。如果他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就不會打開這封信。”他告訴人們,你們總是把這麼多時間浪費在對社交尷尬和傳統慣例的擔憂。如果你參加一個教務會議或者一個聚會,你覺得自己不想待在這裡,那就不要坐在那裡,擔心如果你離開了別人會怎麼想。不要擔心你要編什麼理由。如果你就那樣直接站起來離開,你的大腦自然會想好說辭來解釋你為什麼離開。
顯然他也冒犯了一些人。但是他實在太有魅力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這樣的人。所以,他保留的每樣東西、他做過的每一件事、他檔案櫃裡的所有檔案,他跟人們的每一次互動、和他的所有友情都充滿意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單純的動作。他留下的東西傳達出了很多關於他的資訊。所以重新創造他並不難。他擁有偉大的人格。
沃頓知識線上: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你談到他們的關係就像《單身公寓》(The Odd Couple)裡的菲力克斯·安格爾(Felix Unger)和奧斯卡·麥迪森(Oscar Madison)一樣。
路易斯:有時候我覺得我在寫菲力克斯和奧斯卡。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是在寫《斷背山》,但他們較勁的是彼此的觀點。當他們一起旅行的時候,他們總被誤認為是一對同性戀,因為他們那麼親密。但他倆都是徹頭徹尾的異性戀。他們對彼此的依附比生活裡的其他人都更緊密。但是要說他們像菲力克斯和奧斯卡,也絕對沒錯。甚至他們的個性都與菲力克斯和奧斯卡很像,阿摩司就有潔癖。有人說你走進阿摩司的辦公室,就會發現這簡直是最極端的地方了。桌子中間擺著一支鉛筆,這就是全部。如果阿摩司要工作的話,他會把手伸向旁邊的抽屜,抽出一個本子,與桌子呈直角放置。當工作完成後,他就會把本子收起來。書架上沒有書,牆壁上沒有畫,都是空的。
丹尼爾的辦公室簡直像個災難,他的秘書把他的剪刀綁在椅子上,這樣她就不用四處找了。大家都說,在丹尼爾的辦公室裡,你找不到任何東西,因為裡面一片混亂,在阿摩司的辦公室,你也找不到任何東西,因為裡面什麼都沒有。
他們是兩種對立的人。不管走到哪兒,阿摩司都能為聚會帶來活力。我聽過很多版本的描述。阿摩司走進一間屋子,沒有人注意到他。因為他的外貌和體格並不特別出眾。他有點矮,非常謙遜,而且他也不會穿特別出色的衣服。他就坐在那裡,聆聽五到十分鐘,然後說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就都把目光投射在他身上了。人們說,只要他到場20分鐘後,每個人就會都像飛蛾撲火一樣聚在他的周圍。他總是能夠吸引人們的目光,主導整個局面。
丹尼爾則生性冷漠,遠離人群,非常正式。丹尼爾內心是個法國式的學者,也就是說他比較冷淡。丹尼爾希望混合坦克司機和以色列的空軍飛行員。他為以色列軍隊施了魔法。他完全改變了以色列軍隊的選拔方式,以至於五角大樓都打來電話問,“你們這些人都幹了什麼,就因為這有用?”他寫過一個選拔軍官的演算法,他們現在還在用。那是1954年,他才22歲,簡直難以置信。我曾跟他一起訪問以色列軍隊的基地,他們把他當作上帝一樣崇拜。他們會給年輕兵一個分數,決定他應該到軍隊的哪一個部門,他們把這個分數叫做卡尼曼分數。
阿摩司是一位非常獨立超然的學者。如果他從來沒有遇到丹尼爾的話,你就永遠不會聽說這個人的名字,因為他只會一直運算數學公式。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數學心理學家,你也不會想要知道什麼是數學心理學家。他並非與這個世界有著天然的理性聯結,直到他遇到了丹尼爾。
沃頓知識線上:他們的很多研究目前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仍相當地活躍,這是否會令你感到驚訝?你提到了棒球,但醫療保險或總統競選也有可能有他們的研究存在。
路易斯: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所發現的是思維在各種情況下玩的把戲。他們向人們展示,生活雖然一直將我們置於這些有機率性的情境中,但這些情境也可能為資料分析提供支援,只是我們沒有這樣做罷了。人們並不是天生的統計學家。他們還做別的事情,他們講故事,他們找規律。丹尼爾和阿摩司展示如何運用思維來述說故事、解決不確定性、或者犯錯時的走向。它適用於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要經過大腦。
但為什麼已經發現了這些認知錯覺,它們還會繼續出現呢?因為我們沒有給它們更多的關注。我覺得他們會說,我們在思維研究中發現你的眼睛會欺騙你,你的耳朵會欺騙你。我們甚至可以向你展示它是怎麼欺騙你的。有很多非常真實的視覺錯覺。就算我告訴你沙漠高速公路上沒有水,那是幻影,理智上你知道我說的是對的,但你還是能看見幻影。視覺錯覺不會消失。
可以說,認知錯覺也是這樣的,它不會消失。一個人要想自我糾正是很困難的。阿摩司會說,你能做的就是改變你做決定時的環境,這樣當你犯錯時,其他人就更有可能指出你的錯誤。它所強調的是非獨裁式的決策環境,決策者在做決定時不會認為自己絕不會犯錯,或者依靠不可靠的直覺。
你要在這個過程中設置一些關卡。有一種你可以設置的關卡就是奧克蘭運動家隊所做的,為你要做的那個決定收集優質的資料。如果我在尋找一名棒球球員。這個人看起來像個職棒大聯盟優秀球員,但如果能有一些過去比賽表現的紀錄資料就會更充分了,讓我瞭解一下他成為優秀棒球球員的機率。
並不是說有一個演算法能提供你完美的答案,而是這些資料可以説明你下注,降低賠率,稍微提高獲勝的機率。而且你的眼睛的確會欺騙你。
雖然這本書講的是這兩個以色列心理學家,但是通篇卻用很大篇幅深入探討了休斯頓火箭隊管理部門的思維,因為他們就要開始嘗試僅依靠資料和分析工具來做決定了。即使他們知道最終資料分析也會觸及它的極限,因為很有可能有一半的時間都是錯誤的,雖然不是60%,但大家仍然有點不高興。然後你讓專業的直覺判斷再介入這個過程。現在你又要開始從頭面對認知錯覺了。
沃頓知識線上:你覺得環境在這當中起了多大作用?有些我們覺得在小聯盟中非常成功的棒球球員,去了大聯盟後由於所在的位置不同反而沒有出色的表現。
路易斯:在其他運動中更是如此。當你在洋基隊打棒球的時候,與奧克蘭運動家隊或其他小聯盟球隊相對抗時,很有可能成為一項個人運動。但如果你是一位橄欖球的四分衛球員,你可能在一個體系裡是超級明星,在另一個體系裡反而會被淘汰。如果有人讓佩頓·曼寧(Peyton Manning)跑V型進攻或者做一個奔跑的四分衛是沒有用的。
根本沒有所謂偉大的四分衛,他只有在正確的位置上才能成為偉大的四分衛。這種情況放在其他位置上可能還不是那麼明顯,但是籃球中絕對是這樣的。林書豪離開紐約尼克斯隊後遇到了一些麻煩,這是因為在麥迪森花園廣場的那段時間裡,他處在一個非常正確的位置上。當籃球在他手上的時候,他真的發揮出了最好的狀態。後來他去了火箭隊,在那個位置上他表現得並沒有詹姆斯·哈登(James Harden)好。他被放到了另一個位置上,這個位置對他來說真的很不利。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這個話題挺有趣的,但是個不一樣的話題。
沃頓知識線上:丹尼爾·卡尼曼60年後還能在以色列軍隊中產生那麼大的影響真是難以置信。
路易斯:你還可以在華爾街發現他們的影響。從受監管的選股到指數基金這一轉變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就發表了文章。你還可以在醫藥領域發現他們的影響,醫生們開始對疾病診斷的知識發出質疑。之後阿摩司也開始參與。他們在研究中發現,如果醫生告訴你這個手術可能會治好你的癌症,但有10%的風險你可能會死在手術台上,你就不太可能去做這個手術,但如果醫生告訴你,你有90%的機會可以活下來,你就會做這個手術。我覺得這挺瘋狂的。他們有一個觀點,人們並不是在事情之間做選擇,而是在對事情的描述之間做選擇。
《K@W》授權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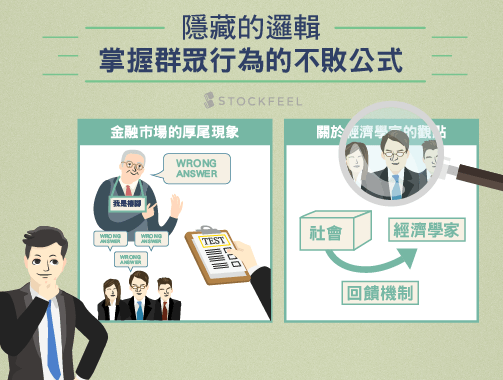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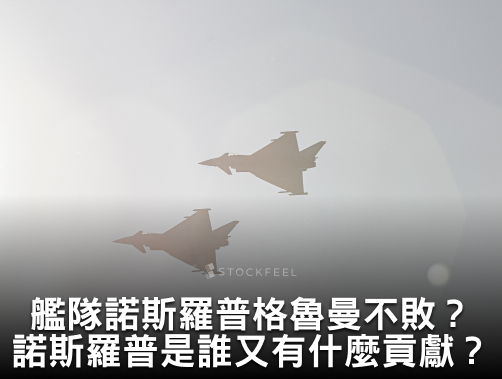
打破CEO神話-四項成功領導者的關鍵特質_-.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