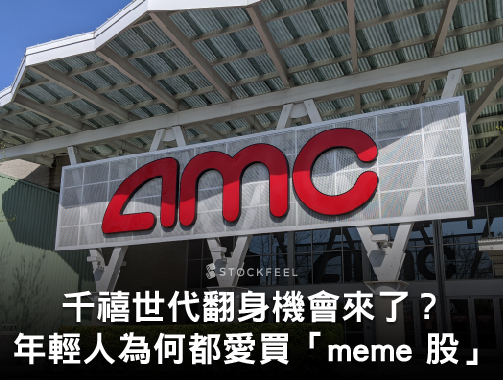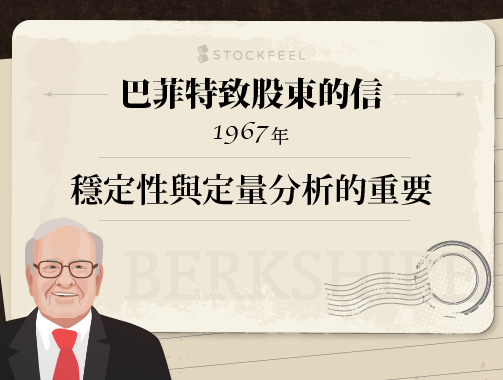2008 年,加州聖克魯斯的兩個年輕人紐納和庫納蒂決定創辦一個共享辦公空間。他們租了一棟大樓,重新裝潢,擺上辦公桌,提供快速的無線網路以及咖啡機。他們將自己的公司命名為 “ NextSpace Coworking ” 。
一個可以改變世界的社區
紐納說: “ 我們真的認為,這會成為一種全新的工作方式。 ” NextSpace 的確為渴望辦公室氛圍的當地自由職業人士提供了工作場所。在短短六個月內, NextSpace 已經小有獲利。很快, NextSpace 在舊金山、洛杉磯和聖荷西開設了新的辦公空間。紐納和庫納蒂也開始尋找風投資本。紐納說: “ 融資代表市場對你的認可。 ”
2012 年,紐納參加了一次共享辦公領域的產業大會,試圖結識一些投資者。大會的發言人之一碰巧是亞當・諾依曼。諾依曼說,他在紐約經營著一家名為 WeWork 的公司,這是 “ 全球首個實體社交網路 ” 。自信滿滿的諾依曼還說: “ 我們將非常快地擴展到全國。 ‘儘管彼時 WeWork 才成立兩年,諾依曼也年僅 32 歲,但該公司已經管理著 30 多萬平方英尺的辦公空間;諾依曼還表示, WeWork 的客戶數量將馬上突破 1 萬大關。 ‘ 我們將共同創造一個可以改變世界的社區。 ”
我們為什麼要投資你?
紐納回憶說,他和風投會面時,對方的第一個問題總是 “ 你打算如何跟 WeWork 競爭?我們為什麼要投資你,而不是 WeWork 呢? ” 儘管據報導 WeWork 每個月虧損數百萬美元,但該公司擴張激進。諾依曼向風投許下的承諾無比樂觀,近乎荒謬,以至於紐納堅信, WeWork 是一個騙局。 “ 我能怎麼回答?難道要我說, ‘ WeWork 在撒謊,你應該投資我們 ‘ 嗎?沒人想聽這些。所有風投都想分 WeWork 的一杯羹。 ”
漸漸地,紐納聽說,在舊金山,在 NextSpace 的附近, WeWork 新開了一個共享辦公空間,而且收費更便宜。其他共享辦公空間的創業者也有相似的遭遇: WeWork 每到一處,就在當地已有的共享辦公空間附近設點,然後用低價打擊競爭對手。有時候, WeWork 還告訴租客,如果他們終止跟別家簽訂合約,他們可以獲得搬遷優惠;更甚者, WeWork 會從競爭對手的網站上獲取客戶名單,然後給名單上的客戶提供三個月的免租期。
紐納只好大幅降價,並提供更多辦公福利,但都無濟於事。 WeWork 的價格實在太低。等到 2014 年底, WeWork 已經融資 5 億多美元。哪怕 WeWork 每個月虧損 600 萬美元,但它的成長速度只增無減。
與其同時,矽谷知名投資者、風投公司 Benchmark 的布魯斯・鄧列維加入了 WeWork 的董事會。鄧列維曾向一名合夥人坦白,說自己並不知道 WeWork 如何才能實現獲利,但是他相信諾依曼。 “ 我們只要把錢給他,他會有辦法的。 ”
也就在這時候,風投告訴紐納說,投資他的公司是在浪費時間;而且如果他們投資了 NextSpace ,就可能會在未來錯失投資 WeWork 的機會。然而,紐納覺得這一切簡直不可理喻。他腳踏實地地創業,但風投卻只想聽豪言壯語。 “ 我們可以讓大家都賺到錢,然後買房、供孩子上學,過體面的生活。 ” 紐納說, “ 但是沒人在乎這些。所有人都想投資下一個馬克.祖克柏。 ” 儘管失望,但紐納並不感到驚訝。然而,紐納沒有料想到的是,有些風投跟這些炒作大師沆瀣一氣,送錢給他們,助長他們的狂言狂語,希望哪個運氣好的賭徒可以一下子賺回本。
2017 年,紐納在書店裡偶然看到一本《富比士》雜誌,封面人物是那個叫亞當・諾依曼的人。報導寫道,諾依曼跟軟銀(SoftBank Group Co, 9984-JP )創辦人孫正義見了面。孫正義對 WeWork 的總部讚不絕口,參觀完之後,他立即草擬了一份臨時合約,承諾向 WeWork 投資 44 億美元。諾依曼說,這筆投資看中的不是我們的財務表現,而是 “ 我們的活力和精神 ” 。
文章還寫道,幾個月後,諾依曼親自前往東京,和孫正義慶祝合作。席間,孫正義問諾依曼: “ 智者和瘋子比賽,誰會贏? ”
“ 瘋子。 ” 諾依曼答。
“ 沒錯。 ” 孫正義說, “ 但是你,還不夠瘋狂。 ”
唯利是圖的風投
起初,風投資本家們仍富有崇高的使命感。他們不是投機者,而是創新的助產士。第一家風投公司旨在尋找和扶持擁有最出色創意的創業公司,為創業者提供所需的資金和策略建議。如在風投家湯姆・帕金斯的指導下,Genentech 成功發明出合成胰島素。帕金斯的公司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曾向 Genentech 投資過十萬美元。帕金斯要求加入 Genentech 的董事會,接著每週會花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在創業公司的辦公室裡查看支出報告,教訓初出茅廬的高層。在隨後的幾年裡,凱鵬華盈投資並扶持過亞馬遜(Amazon, AMZN-US)、Google、昇陽電腦和康柏等科技公司。
在帕金斯之後,風投產業已經成倍成長,其中不斷成長的還有整個產業的貪婪之心與憤世嫉俗之風氣。如今,幾十家大型風投公司掌控著整個產業。雖然風投總吹噓自己以追尋激進的商業創意為使命,但他們似乎也就是在炒作矽谷的趨勢——而且他們的管理監督也越來越淡化,使他們的投資更像是一場賭博交易。目前在史丹佛工程學院任教的創業家布蘭克說: “ 我看到整個產業越來越像唯利是圖的暴民。現在的風投根本不關心公共利益。他們只對提高自己的利潤和追逐風口(註:風口指投資機會或趨勢)感興趣,其他事情一概不關心。他們浪費了數十億美元,而這些錢本可以用來發展真正可以幫到人們的創新。 ”
這種抱團式的服務自我的方式,成就了一群風投資本家。 2020 年 1 月,美國風險投資協會高呼過去十年是 “ 高速成長 ” 的 “ 創紀錄的十年 ” 。在這期間,協會成員共向創業公司注資近 8,000 億美元, “ 為明天的經濟注入了活力 ” 。最近幾十年,風投的賭注越下越大。一名知名風投資本家透露: “ 說實話, 3,000 萬或 4,000 萬美元以內的投資沒有多少意義。不管你投資多少錢,盡職調查、董事會開會的時間等等,工作量都一樣。 ”
風投產業的批評者發現,最近風投又開始向一家十分值得懷疑的創業公司大把投錢。先前曾有血液檢測公司 Theranos,在被曝光是騙局之前,獲得 7 億美元投資。出售所謂帶 Wi-Fi 功能的果汁機 Juicero ,曾融資 1 億多美元,甚至 Google 也參與過投資,但僅堅持了四年。
風投產業獨鍾挹資創業公司
漸漸地,風投產業越來越痴迷於創造 “ 獨角獸 ” :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創業公司。其中的確是有一些獨角獸獲得了持久的成功,但更多的獨角獸——包括 Uber 、數據挖掘巨頭 Palantir 和醜聞纏身的軟體公司 Zenefits 等等,似乎從未有過實現獲利的切實可行計劃。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肯尼說,感謝風投的慷慨, “ 虧錢企業可以存活更長的時間,打擊市場現有企業。 ” 在傳統資本模式下,最有效、有能力的公司將會獲得成功;而在新資本模式下,融資越多的公司才是贏家。這樣的公司往往會 “ 破壞經濟價值 ” ——即摧毀實實在在的競爭對手,並創造 “ 無益於社會的革命 ” 。
許多風投資本家說,他們也別無選擇,只能向創業公司注資。為了讓矽谷創業公司成為真正的獨角獸,他們只能掃清競爭對手,然後成為市場主導品牌。軟銀的執行合夥人傑夫・豪森博爾德說: “ Uber 成立後不到一年,市場上已然冒出三百多個模仿者。保護你的公司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融資來加快發展步伐。 ” 風投資本家還說,更重要的是,大型風投公司都盯著同一個交易,試圖說服同一個受青睞的創業者接受他們的投資。為了贏得創業者芳心,風投只能對他們有求必應。
特別是在矽谷,創辦人通常更偏好那些承諾不過多干預或不會提出太多問題的風投資本家。於是,風投拋棄當年帕金斯的做法,開始宣揚,他們 “ 對創辦人友好 ” ,對例如每週在公司辦公室花一下午時間開會這種事情不感興趣,也不會質疑年輕的執行長的決策力。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喬什・勒納說: “ 如今承諾對創辦人不離不棄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 ”
帕金斯那個年代的風投資本家曾經以建立良好的治理和對公司的密切關注而感到自豪;而如今的風投則更傾向於鼓勵創辦人的天馬行空。在不到 20 分鐘內就決定向 WeWork 投資 44 億美元的軟銀掌舵人孫正義,正是這種風格的最佳體現。 2016 年,他開始籌建千億美元的願景基金。一名軟銀前高層說: “ 孫正義決定要向年輕公司的血液中註入一劑古柯鹼。你找到一個創業者,然後告訴他, ‘ 要不馬上接受我給你的 10 億美元投資,要不我就把這筆投資給你的競爭對手,而你則黯然退場。 ‘ ” 這名軟銀前高層接著又說: “ 風投資本越來越像買彩票。孫正義可能不是一個特別深思熟慮的人,但他有一個優勢:致力於購買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彩票。 ”
被貪婪腐蝕的資本
隨著 NextSpace 的消亡和 WeWork 的擴張,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針對 WeWork 的掠奪性策略和反常文化的傳聞越盛,諾依曼越是受風投追捧。儘管 WeWork 公司內部文化混亂,但 WeWork 的估值每年都在翻倍。
諾依曼先後創辦過幾家公司,包括銷售可折疊高跟鞋的女鞋公司以及生產帶護膝的嬰兒服公司 Krawlers 。在這兩家創業公司都失敗後,諾依曼和合夥人麥克凱爾維在布魯克林租了一個辦公司,分成小空間,然後將自己包裝成共享辦公空間創業者。當潛在投資者來參觀時,諾依曼讓員工假扮租戶。 “ 他真是瘋了,但就是這樣的瘋子才能讓你相信,他可以成功。 ” 另一名風投說, “ 他是我見過的最有魅力的推銷員。 ”
2014 年,諾依曼已經收到大量風投遞來的橄欖枝。最後,諾依曼宣稱:自己只會和願意給予他多數投票權的投資者合作。已經是董事會成員、如今也是諾依曼導師的鄧列維當即覺得,這種不受約束的權力是一個糟糕的注意。他曾試圖勸說諾依曼放棄自己的要求。他還在董事會議上,敦促 WeWork 的其他董事否決諾依曼的要求,還援引阿克頓勳爵的話稱: “ 權力容易腐敗,絕對權力必然會腐敗。 ”
諾依曼在會上說自己不在乎阿克頓說過什麼,而董事會的其他人也無一人站出來支持鄧列維。鄧列維本可以在這時候辭去 WeWork 董事會成員一職或公開提出反對。他之前就這麼幹過。但這一次,鄧列維沒有辭職。他的一位同事說,辭職 “ 將會是這世上最愚蠢的決定。我們在 WeWork 估值約 8,000 萬美元的時候做了投資,現在 WeWork 價值 150 億美元,然後我們要在這個時候選擇離開嗎? ” 最後,鄧列維只好從了其他投資者的大流,把投票權給了諾依曼。
絕對的腐敗
WeWork 內部有許多問題。這些與鄧列維和其他董事會成員應該也脫不了關係。 2018 年春,董事會得知一名公司高層捲入性醜聞訴訟。董事會還允許熱衷於衝浪的諾依曼從 WeWork 的資金中拿出 1,300 萬美元,用於投資跟 WeWork 業務毫無關係的一家製造人工波浪池的公司。董事會還批准了諾依曼的股票出售和貸款。當諾依曼的妻子麗貝卡突然宣佈公司內不准吃肉時,董事會依然默不作聲。
WeWork 的前高層說,及至 2018 年, “ 我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確保諾依曼不會幹出蠢事或非法之事——董事會知道諾依曼是融資的關鍵。只要估值一直在漲,他們就不會冒險惹諾依曼不快。 ”漸漸地, WeWork 雖仍在快速成長,但曾經願意公開替諾依曼說話的董事會成員,開始拒絕媒體採訪。
等到 2019 年初,諾依曼連董事會議都不出席了。但其他董事依然不聞不問。一位專業投資者說: “ 你可不希望落得一個對創辦人不友好的名聲。 ” 大多數風投都覺得,他們可以忍,因為 WeWork 正在籌劃上市。一旦上市,股東和監管機構勢必會約束諾依曼。而董事成員則可以出售股份兌現,然後跟 WeWork 徹底說再見。
IPO的核心是一份名為 S-1 的文件。該文件由董事會批准,主要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大眾列明公司的財務細節。諾依曼在文件中加入了一些荒唐的條款,比如上市後,他有權開除和駁斥任何董事或員工、獲得額外價值 18 億美元的股票等等。眼見著上市之後,錢可以進來,麻煩可以擺脫,鄧列維也簽署了這份 S-1 文件。但是, WeWork 的很多高層擔心, S-1 文件公開後,可能會引來麻煩。然而,他們也選擇保持沉默,因為 “ 財富近在咫尺, ” 一名前高層說, “ 我們都有意選擇無視,貪婪佔據了上風。 ”
“ 而且更關鍵的是,如果上市成功,大家都發財致富了,那麼科技產業和華爾街的所有人都會稱讚諾依曼是一個天才,而 WeWork 就是美國資本主義運作的範本。 ”
翻臉無情
風投資本家加入一家公司董事會後,他們將承擔法律義務,一視同仁地保護所有股東,以及必須保證不會將自己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之上。這項義務最為關鍵,因為董事對公司的行為擁有最終權力,而且從根本上來說,他們代表了未受邀進入董事會的每一個人。如果董事發現任何可能對哪怕是最小股東造成損害的端倪,根據法律規定,董事都必須將真相說出來,即便保持沉默對董事自己有經濟利益。
但是證明董事違反這一法律義務卻相當複雜。雖然在上市公司內,這個標準可以得到嚴格執行,但是私有公司就是另一番情景。在私有公司內,董事會成員通常包括公司創辦人、風投和創辦人的朋友等。隨著風投產業越來越集中化,這種抱團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如今,大多數的風投交易都已經 “ 財團化 ” ,或者說分到一杯羹的一直都是那幾家大公司,這種 “ 聯盟式 ” 的氣氛促使風投在面對不道德行為時,選擇保持沉默。
2019 年 8 月 14 日, WeWork 的 S-1 文件正式發布。一名公司前高層說: “ 諾依曼夫婦覺得,他們終於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願景。 S-1 文件是他們的偉大傑作。 ” 然而,股票分析師、記者和投資者們對這份文件並不滿意。哈佛商學院教授利亞茲表示,文件暴露了 WeWork 的 “ 錯綜複雜的企業結構、持續的虧損、大量衝突以及完全不存在的企業治理 ” 等等。此外,利亞茲還稱, S-1 文件並未提供許多的傳統財務細節。她說,直覺告訴她,這份 S-1 文件 “ 具有誤導性,可能是騙局 ” 。
在 WeWork 準備向機構投資者進行推廣活動前兩天,有人聽說有媒體即將曝光諾依曼的一些醜聞。董事會為此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並決定延遲IPO。但直到此時,仍沒有董事願意跟諾依曼正面對峙,甚至還告訴諾依曼,自己會支持他。但 WeWork 的高層坐不住了。他們聯繫上董事會,要求董事會承認,諾依曼是一個累贅。如果諾依曼繼續當這個執行長,公司將無法上市。諾依曼成了大家財路上的絆腳石。
一旦風投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危在旦夕,他們的行動將比誰都快。摩根大通(JPMorgan, JPM-US)的迪蒙跟諾依曼說: “ 為了公司,你最好辭職。如果你同意,我們不會虧待你。 ” 沒過多久,鄧列維也告訴諾依曼,他會毀了公司。如果他不辭職,他會破產。鄧列維還斥責諾依曼卑鄙無恥,威脅稱如果不辭職的話,自己會打斷他的胳膊。
9 月 24 日,諾依曼辭職。兩名 WeWork 高層接任臨時執行長;幾天內,他們辭退了十幾名諾依曼的親信。 WeWork 前高層說: “ 諾依曼浪費公司資金的時候,董事會默不作聲。現在,諾依曼威脅到他們的利益了,他們就馬上翻臉無情。 ”
本來這時候,董事會可以接手重組公司。但是,他們並沒有。相反,董事會找來孫正義接盤 WeWork 。根據交易, Benchmark 可以獲得大約 3 億美元收入,諾依曼也可以拿到 7.25 億美元。了解鄧列維和 Benchmark 的知情人士透露,到最後,該公司的投資依舊安然無恙。遭殃的只是 WeWork 的員工和其他少數投資者。
風投依舊有錢
當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時, WeWork 的商業模式變得不堪一擊。年初以來, WeWork 已裁員數千人。但 WeWork 說,該公司預期會在 2021 年實現獲利。分析師也覺得,從長期來看,該公司有望獲得成功。然而,在許多方面, WeWork 仍舊一團糟,董事成員之間對簿公堂。如果 WeWork 能成功,那成功的原因大概也會和之前快速成長的原因差不多: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風投資本。
但是,風投資本家說, WeWork 的鬧劇給共享辦公空間產業蒙上了一層陰影。著名風投史蒂夫・克勞斯說: “ Theranos 的失敗,摧毀了血液檢測創業領域。產業裡有好創意的公司想融資都變得幾乎不可能。 ” 雖然 WeWork 不是因為欺詐而是管理不善才導致失敗,但也同樣讓投資者對其他共享辦公空間創業者心有餘悸。三月初,卡車創業公司 Nikola 被迫賣身競爭對手, Nikola 的總裁說, WeWork 的崩潰嚇走了潛在投資者。 “ 有很多非常棒的創業者,但他們都說, WeWork 之後,融資變得更加難。 WeWork 毀掉的不止是共享辦公領域。 ”
幾十年來,風投資本家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伯樂。但是 WeWork 這樣的例子,讓人們再也無法相信,風投能在貪婪與創新之間找到平衡。相反,風投似乎越來越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見利忘義,青睞狡猾的中間人和誇大其言論者,而不是獎勵勤懇的員工和富有創意的商人。
NextSpace 聯合創辦人紐納說: “ 錯不在諾依曼。每個人都知道,他兜售的東西看似美好但無法實現。他也從來沒有掩飾自己不現實的樂觀主義,從來沒有假裝理智、腳踏實地。在創業圈裡,我們不缺富有創意的企業家,但漸漸地,你會看到他們在風投的慫恿下接受大筆投資,然後做出錯誤的選擇,不計代價的追求成長。然後, ‘ 砰 ‘ ——完蛋。最終,你開始明白:無論發生什麼,風投依舊有錢。 ”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