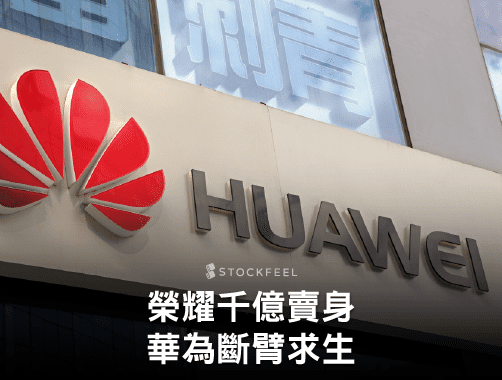2020 年沒有比內捲更出圈的人類學術語了,它用來形容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用內捲化來形容近年的創投產業格外形象。那些用名校學歷、海歸經歷、大公司履歷作為敲門磚進入投資產業的投資經理,在 2020 年,只剩下擠進前端基金或退出產業兩種極端選擇。產業趨冷、缺少風口(註:風口指投資機會或趨勢)的創投產業,養活不了中小投資機構,它們競爭不過前端基金,大多數成為了不投資只退出的 “ 殭屍基金 ” 。而小型基金不需要經理人,現在流行 LP(出資人)自己管理。
晉升的管道又如此狹窄,頂級投資機構需要的經理人就那麼多。紅杉資本的經理人,約有二、三十位,其他前端基金,規模也大致如此。創投產業變為了贏家數量恆定的白熱化競爭。夾在中間的腰部經理人,不是 “ 生 ” 、就是 “ 死 ” ,沒有中間值。
哪裡是庇護所
劉唯幾乎一整天都泡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裡,翻看華爾街的商戰風雲、新零售的創新模式,線下消費的業態變化⋯⋯。在這裡他維持著一種事實上的體面,他依然是關注中國商業最前端變化的一小群人。但是,走出圖書館大門,他不過是一位失業近一年的待業者罷了。 2019 年末,他將辭職申請在傳給上司,辭呈裡他表達了對公司的感謝和想要創業的想法。這是一種客氣且委婉的離別話術。他對上司的真實看法是 “ 他不懂投資,有些事情要問我,還經常瞎指揮 ” 。
劉唯是一家人民幣基金的投資經理,身形纖瘦,喜歡帶無框眼鏡。見面當天,他穿著牛仔褲和橫格紋羊絨衫,背著黑色雙肩包。如果他不開口說話,感覺是一位學生。當他開始表述,屬於經理人身上的習性逐漸展露,它很好識別——慣常性的對事情進行判斷「這件事情做不大」以及總是要求別人證明自己「這個模式能走通嗎? 」
至少在疫情到來之前,離開供職近兩年的投資機構,是劉唯認為正確的決定。資本市場的熱度日趨冷卻,鯨準發布的白皮書顯示,從 2017 年開始,創投市場的交易事件逐年下降。到 2019 年,創投市場總交易量已經降至一年不到 4,000 起,降幅達到 61.9% 。收縮、調整的創投產業,無法滿足員工的 “ 錢景 ” ,連續兩年,劉唯沒有調整過薪水,薪資不到 28K (人民幣,下同)。
劉唯不是個例,大批經理人 “ 消失 ” 在 2020 年。投中研究院的數據顯示, 2020 年度私募基金管理人取消事件已達 808 件。一批經理人還未來得及成長,已經被褪去的大潮卷回至岸邊。投資機構給予經理們的成長窗口期也日趨縮短。之前那些掃樓、參加項目路演活動的投資經理,還擁有可以成長為投資總監的夢想。如今,能否留下的標準被制定的很清晰,投出過 10 億美金的企業嗎?參與投出過 10 億美金的企業嗎?
成人世界最確定的事情是不留無用之人。創投產業不需要沒有知名case的投資經理。那些沒來得及證明自己的經理人,已經被推到轉行的邊緣。
他們中的一些人,轉型之路不難察覺。投資經理們已經悄悄的在朋友圈賣起了保險,還有一些轉型做了微商。經理人之間也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很久沒有某某的聲音了,那應該是不在投資產業了。丁峰的轉型之路同樣波折,他經歷過三重身份的轉換,經理人——創業者—— FA (財務顧問)。就像他曾經關注的投資賽道一樣流動、多變,從無人貨架、人工智慧到今年大火的教育。還是經理人的時候,丁峰會跟新認識的人講,「你不認識我嗎?可以去百度(Baidu, BIDU-US)上搜尋我的名字,上面有我的資訊」。 2020 年,這樣的開場白已經沒有了,他會跟約見的創業者主動介紹自己。
浪退了、風停了
過去 5 年,整個一級市場空前膨脹。根據鯨準數據, 2015 年到 2020 年一季度,中國股權投資市場交易金額總量達 7.5 兆元。交易數量的峰值出現在 2015 年四季度,達到了 4,691 起。劉唯是在市場熱門的時刻加入股權投資產業。 2015 年 6 月,他從清華法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成為一家人民幣基金的管培生。按照他預期的職業規劃,他將會是一名投資經理。然而,個人意志在產業變化面前總是微不足道。
2015 年的A股市場冰火兩重天。 6 月初,上證指數漲到 5,100 點,創業板指數漲到 3,900 點。火熱的氛圍在 6 月中旬戛然而止,監管機構清理配資,下發文件明令禁止證券公司為場外配資提供證券交易接口。資金管道突然切斷,投資者聞風踩踏。A股市場出現了漫長的下跌期直至次年 1 月,還出現過 “ 千股跌停 ” 的景象。
股災發生,二級市場的估值回調,不確定性迅速傳導向一級市場。人民幣基金開始 “ 緊急剎車 ” ,簽了TS的項目也不打款,它們後悔給的估值太高了。團車創辦人聞偉經歷過這樣的時刻, 2014 年團車項目估值 1 億美金, 2015 年估值 10 美金,直接翻 10 倍。
資本市場行情好的時候,人民幣基金在市場上抬估值,搶項目,一些美元基金早期投資的項目,後期拆分VIE架構,轉向人民幣基金募資的情況並不罕見。後者給的估值遠高於市場價格,因為二級市場給予的溢價更高。當年創業板的本益比高達 140 倍,正是估值太高,創業板的本益比被稱為 “ 市夢率 ” 。
等到劉唯進入投資產業的時候,方向轉變,人民幣基金的主要任務是避險,它們不敢輕易投資,在業內它們被叫做 “ 殭屍基金 ” 。用真格基金創辦人徐小平的話說,人民幣基金的出資人(LP),多數錢都是來自股市,股市不穩,立刻就傳導到基金方面。
外部環境變了,劉唯沒能如願的以投資經理的職位開始他的職業生涯。管培生結束後,他被分配到投後,負責法務工作,理由是「基金的重心轉到投後,控制整體風險,希望被投項目有好的退出成績」。負責投後,劉唯不參與投資,只加入投資之後的風控環節,管控被投項目的法律風險。他對投資——以知識、視野、判斷力作為主要工作依據的職業想像,以現實、不遂人意的起始作為開場。
這只是他坎坷職業履歷的起始。日後,他想轉做投資經理的時候,數次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證明你能夠成為一名投資經理,你都沒有做過」。他的困境同他接觸的創業者何其相似,都要證明自己如何能夠做到。
誰有話語權
投資產業流行講 “ 二九八 ” 效應,前端基金拿走 98% 的市場佔有率,中小投資機構能夠拿走的只有 2% 。雖然今年出現過中國大基金集體失手泡泡瑪特的情況,但那是偶然中的偶然。現在的市場,平均融資額不斷上漲,更趨向於集中的項目標的。那是屬於少數項目的狂歡,風險投資更願意擁抱確定性,那些證明過自己的創業企業拿走了市場上的大部分錢。優質企業總是跟前端基金相伴成長,其中不僅僅關於錢,還包括名譽背書。被前端基金投資,等於在產業和媒體面前公開亮相,根本不愁下一輪融資。
創投市場不需要小型基金,那些憑藉資本市場火熱之際,找到LP融幾百、幾千萬美元,創辦小基金的模式已經被拋棄了。小而美的投資時代不存在了,募資 5 億美金以下的投資機構沒有未來,這一點已經成為創投產業的共識。丁峰在 2019 年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的一期基金創造出 4.5 倍的報酬率,但是二期募資階段,LP已經不願意出錢了。他的投資機構就活了 3 年零 2 個月。
2016 年初,一位富商願意出資 1,000 萬美元做他的LP,憑藉這筆資金,丁峰得以進入創投產業。但也因為單獨LP占基金的比例太大,出現了LP一直插手投資項目的情況。「他總是急著賣掉項目,A輪融資之後就想賣掉」丁峰因為項目投資週期的事情幾次跟LP意見不合,最後二人一拍兩散。對於二期基金募資失敗,丁峰有自己的看法「整個市場都在擁抱確定性,誰需要風險投資?LP的錢用來買茅台,東南亞炒樓不行嗎?」一定程度而言,丁峰幸運過,在市場火熱的情況下,獨立操持過一家小型基金。劉唯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被動的跟著資本的方向變換。
2016 年,他加入一家負責新三板項目的投資機構,原因很直接「它們願意給我投資經理的職位」。出差、看項目、做盡職調差,劉唯初步接近了夢想中投資經理的工作。但是,新三板因為流動性差,不方便退出,曇花一現的火熱過就迅速冷卻了。現在沒人談論新三板,劉唯自己也不願意談論。三年前,劉唯又一次更換名片, 他新加入了一家人民幣基金。這份工作經歷,讓他遇到了職業生涯中最心動也最讓他遺憾的案子。 2018 年他看過一個高校團購的項目,模式類似今年大火的社區團購,只不過消費場景是高校。
兩名石家莊創業者創辦了這個項目,路演階段其他經理人沒有相中該項目,但是劉唯看中了。他向主管極力推薦,沒用,最終沒投。「他過高估計了高校團購的擴張速度,認為是重資產項目,其實慢一點也能活下來」劉唯認為是領導高估困難,令他錯失項目。一位投資經理,沒有成長為總監級別,通常情況下不享受項目分成。而如果沒有成為合夥人,意味著沒有項目投資與否的最終決定權。
其實,按照約定享受分成也不見得一定能拿到,那隻是約定的獎勵。經理人王磊在疫情期間,一度在朋友圈賣保險度日,沒有離職,就是寄希望於自己參與投資的項目能夠順利退出,他能拿到 8% 的獎金。但是,當他供職的機構,退租了光華路的辦公空間,變成了無固定辦公地點的 “ 散裝 ” 投資機構時,他已經不報希望了。「機構已經事實上死亡了,合夥人們現在就是尋找各種方式退出項目。」王磊決定重回百度上班,他放棄了項目獎勵,「耗不起」。項目沒有退出之前離職,沒有項目分成。這是人民幣基金約定俗成的規矩。
經理人的新去向
劉唯不在咖啡館喝咖啡了,出門攜帶一個 500ml 的水杯,裝滿白開水,經濟、實惠。一年的待業期,讓他有了經濟壓力。今年 4 月,他從石家莊返回北京,發現疫情持續的時間,超出他的預期。離職前他打算做一個短片項目,外國人出鏡,內容形式還沒想好,獲利模式已經想清楚了,為教育機構導流。但是,疫情導致五道口的外國人很少,他找不到合適出鏡的主播。買了一堆影片設備之後,項目暫時擱置下來。
他曾考慮要不要先去幾家網路大廠工作,但是它們的薪資和職位不符合他的預期。大公司的法務,薪資和成長空間不高。經理人轉型的難題之一是不願意自降身價,導致可選項不多,離開投資產業,他們的職業選擇是逼仄和局促的。劉唯還是想自己創業,下半年他市調研究餐飲項目,已經有了鍾意的商業模式,他說等疫情結束,明年吧。比起金錢壓力,他更急切的想證明自己。他研究生期間的同學,因為做區塊鏈項目,已經身價過億。來自熟人間的比較,帶來的壓力,更沉重。
丁峰正忙著跟創業者打官司,今年 7 月,他幫一位創業者融到 1,500 萬元,按照合約約定他收取 5% 的財務顧問費用。但是創業者只支付給他 3% 的費用,因為丁峰是從其他 FA 機構轉手接到的項目,創業者以中途換人為由,不認帳。項目的經理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不知道。丁峰也理解,交易談成了,沒人願意給仲介支付費用。 FA 今年的生意也不好做,有的 FA 經理一年也沒撮合成功一個項目。
以前 FA 是撮合交易,創業者融不到錢,不收取費用。今年,這樣的模式不適用,因為好項目少,融到錢的項目更少。為了生存下去,有 FA 機構創造性的拓展了諮詢業務,創業者來諮詢融資問題,先收費兩萬元。丁峰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業務模式,他覺得不太體面。王磊重回百度,職級 P7 ,跟他離開時候的職級一樣。相當於四年投資經歷沒有對他的職業生涯有實質性的提升。
光鮮亮麗下的黯淡
過去幾年,媒體報導了太多財富故事,講述太多機構合夥人的智慧人生。這些只是投資產業最光鮮,最被外界所稱道的,同時也是最稀少的人生經歷。投資產業大多數人只是投資機構的眼睛和耳朵,用來輔助尋找市場上的資訊和捕捉風向。如今,創投產業的風勢漸小,不需要那麼多聽風者了。通往財富世界的道路總是狹窄而擁擠的,就像這個世界太多人想成為賈伯斯,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擁有屬於自己的蘋果(Apple, AAPL-US)。
《36氪》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