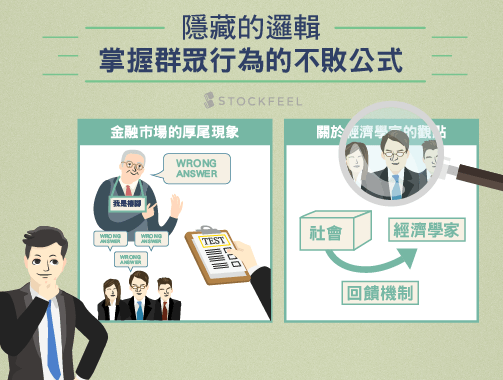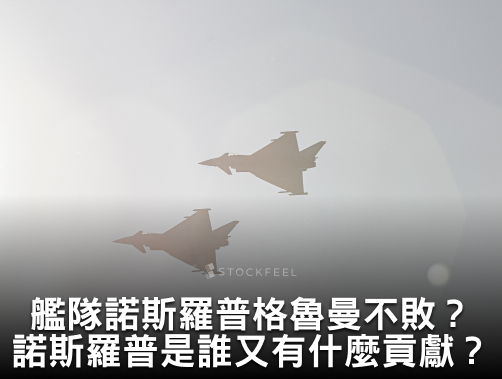很久沒有看到這樣“零負評”的動畫電影了,就像現在稱讚美女一定要加上“零死角”的定語一樣,這個世界上素來不會缺少苛刻挑剔的批評家,卻罕見讓非議蕩然無存的乾淨回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出產於迪士尼(Walt Disney, DIS-US)的第55部動畫長片,本身已經不再帶有迪士尼的符號式桎梏,充滿自我革命的蓬勃氣色。
商業市場就是如此奇妙,在經歷漫長的競爭與合作關係之後,迪士尼支付巨大的財務風險將皮克斯放入購物車,並挽留住約翰·拉薩特成為兩家公司共享的創意長,這種融合讓迪士尼和皮克斯都有了一些新的變化。

從左到右:皮克斯的數位科學家艾德文·卡特姆、皮克斯的前任CEO賈布斯、皮克斯的創意長約翰·拉薩特
比如迪士尼出品的《無敵破壞王》,無論是從設定還是劇情而言,其實有著皮克斯的《怪獸電力公司》的影子。而掛名於皮克斯旗下的《勇敢傳說》,則又隱隱透露出迪士尼擅長的女孩夢幻風情。
當然,從結果出發,皮克斯尚在消化和適應的階段,2006年的《賽車總動員》作為迪士尼持續多年力主推進的一個合作項目,最終票房數字為皮克斯迄今為止的倒數第二,2012年的《勇敢傳說》更是災難,連《怪獸大學》都遭受牽連,沒能過皮克斯8億美元的歷史票房均線。
迪士尼的逆襲則有目共睹,這在2013年的《冰雪奇緣》上觸及頂峰。只是,這部勝於美術和音樂的“又一個公主的故事”依然沒有離開迪士尼的舒適區,儘管它用力吸取了皮克斯“用成人的視角構建童話,用孩童的語言娓娓敘事”的特長,票房及衍生品的成績也相當輝煌,但迪士尼的表現的確只能說是再度接近了自己的極限,而非超越了它。
《動物方城市》的橫空出世,卻是自我革命的典型產物,它甚至擺脫了迪士尼在架空世界觀的建構上一貫的貧瘠,將政治寓言和童話故事合二為一,同時滿足家庭兩代觀眾的欣賞取向,而這正是好萊塢所推崇的“合家歡”電影的追求效果。
第一個謊言:社會可以被設計
“Zootopia”顯然是“Utopia”的變體,這個起源於古希臘哲學時代的概念性名詞經過多年的解釋和演繹,已經如同應許之地那樣變得面目模糊而陰霾密布,以至於批判烏托邦轉而演變為近代文學的某種主流姿態,《駭客任務》亦道出眾人的共同憂慮:若有完美,必有謊言。
動物方城市的理念“Anyone can be anything”則是《獨立宣言》“All mem created equal”的變體,或者說得更加直白一點,動物方城市的魅力和引力,與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所定義的“美國夢”是一脈相承的:“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麼樣的社會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種得天獨厚的機遇…,他有權生存,有權工作,有權活出自我,有權依自身先天和後天條件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這塊以移民建國(5515-TW)並能持續吸引全球人才越洋奔赴的世外土地,正是基於“人人皆可成功”的普世信念而運轉自如。
從十九世紀開始,當革命的暴戾火焰與階級的傳統枷鎖成為整個歐亞大陸僅剩的兩個選項,北美那塊以移民建國的世外土地,就被歷史託付了烏托邦的角色。
於是,我們很快遇到了烏托邦的第一個謊言:它無法被設計。
以柏拉圖的《理想國》為起點,空想派學者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憑藉智慧,人類可以設計出一種沒有瑕疵的社會制度”,從傅立葉到歐文,從布朗基到馬克思,烏托邦的參數愈來愈具體,實現它的方式也愈來愈激進,而流星的隕落,也一個比一個聲勢浩大。
動物方城市及其藍本美國無法倖免於外。動物方城市賴以生存的“和平條約”—它使草食動物與肉食動物有了相處的共識,並維繫起了一個走出蠻荒時代的現代文明—像極了美國人念茲在茲的國父傑作,即《獨立宣言》及其衍生出來的合眾國律法體系。
但是,一紙文本框架的偉大,並不能就此永葆子民的安康,就像機器圖稿的美妙絕倫,也要依賴每一顆零件的打磨和操作機器的手藝。《動物方城市》的矛盾和衝突所隱喻的,是那些經過設計之後的複雜運轉,你可以看到傲慢與偏見,也可以看到種族或是信仰歧視,還可以看到自由與權利的相互摩擦。
兔子茱蒂和狐狸尼克的初次相遇,是在一間由大象開設的冰淇淋店裡,大象拒絕向名聲不佳的狐狸出售冰棒,並拿出一張寫有“每個動物都有權拒絕向其他動物提供服務的權利”的告示作為法律支撐。
這並不是虛構的場景。在美國,許多商店都有“We reserve the right to refuse service to anyone(我們保留拒絕為任何人服務的權利)”的標語,這是憲法保障個人自由和私有產權的條文,比如一個醉漢,便利商店可以拒絕為他服務,一個衣冠不整的男人,也不被允許進入對穿裝有要求的高級餐廳。
比如,美國曾發生過多起有著宗教信仰的蛋糕店店主拒絕為同性戀情侶製作婚禮蛋糕的司法案件,前者認為違背個人信仰去用雙手烹飪歌頌同性婚姻文案的糕點實在太過痛苦,他們有權不被強迫做這麼一件難受的事情,而後者則搬出《民權法案》指控蛋糕店的歧視行為,並在政治正確的語境下贏得了從勞工局到法院再到主流民意的支持。
除非虛偽到自認為先知的地步,否則我們應當承認,在類似事件上做出價值判斷的難度之高,恐怕並不適合在短期內設立底線之上的規則。就像美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終在去年獲得最高法院的認可,但是他們仍然必須尊重“人們有討厭同性戀的權利”,而不是提出將保守主義者統統扔進監獄的主張。
《動物方城市》的處理細節仍然令人讚嘆,它沒有讓身為警官的兔子茱蒂使用權力強迫大象把冰棒賣給狐狸,而是挑出了大象違規操作的行為,以和解交易的形式讓大象不得不配合這一次的例外要求。
這就到了烏托邦的第二個謊言:救世主是必要的。
第二個謊言:救世主是必要的
顯而易見的是,冰淇淋店的大象可以繼續“歧視”那些令他討厭的顧客,他並沒有被兔子茱蒂說服,以後進店的狐狸大概依舊會被他拒絕服務。而兔子茱蒂在幫助自己萍水相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自己誤解買單—的狐狸尼克之後,也不會繼續駐店設法解決大象的政治錯誤問題,這既非她的職責,也不在她的能力範疇之內。
事實上,與超級漫畫英雄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潮流不同,《動物方城市》缺少對於一招制敵的路徑依賴,兔子茱蒂從事警察工作也沒有多少懸壺濟世的初心,她只是恰好將這份職業作為個人理想並堅持始終,是自私早於無私的個人主義表率。
兔子茱蒂之所以查收失踪案件,是因為她不甘心做交通管理的平庸工作—儘管這種預設職業不平等關係的心態本身就有些微妙的失語—但是當她成為這座城市的英雄時,她才發現自己其實搞砸了一切。
只有身為“幕後黑手”的綿羊副市長,才絞盡腦汁的要為動物方城市樹立一個英雄,她以為上進而又積極的兔子茱蒂會毫不猶豫的接受這份遲來卻應得的嘉獎,卻算錯了這隻兔子的本性:她只是想加入這座理想中的城市,並沒有任何動力去改變這座城市。
而讓草食動物凌駕於肉食動物之上的反派陰謀,則與《動物莊園》裡“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的黑色幽默遙相呼應。動物方城市絲毫沒有康帕內拉和莫里斯筆下那種扁平化、公有化的烏托邦結構,其反差之處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設想:所有幸福都是被安排好的。

喬治·奧威爾的一生其實從未去過蘇聯,但他卻是世界上最了解蘇聯的人之一
因此,“蒙冤”的獅子市長也有著一張典型的政客面目:他囚禁那些失控的肉食動物,目的只是保住地位以及避免引起民眾恐慌。只是,這種心思過於好猜,才有羊副市長的精巧策劃,一步一步的製造對立,把獅子和其他肉食動物推下深淵。而身為“壞蛋”的羊副市長,則有著長期不被重視與尊重的職業生涯,她明白自己之所以被委以副市長的高位,只是因為獅子市長想要爭取草食動物的選票罷了。
一切都逼真得栩栩如生。
至於兔子茱蒂是如何掙脫成為一枚掉在棋盤之外的棋子,其實已經不太重要了,動物方城市恢復往昔的生機,卻不會將兔子茱蒂的雕像樹滿全城,這裡依然吸引著追求夢想的動物,也依然存在欺詐、犯罪和黑幫,你來或是不來,它都在那裡,不增不減。
如果說救世主意味著人們心存僥倖而不切實際的憧憬—盼望有種超越常規的力量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那麼承認缺陷則是另一種現實層面的妥協和機智。就像維護一個多元性的城市—一個連兔子和狐狸都能當上警官的城市—說服性,要遠勝於一個有能力將歌頌多元性的偉大語錄貼遍大街小巷的領袖。
機會平等,優於一切。
第三個謊言:人人皆為螺絲釘
美國民權運動的歷史極其短暫,馬丁·路德·金高舉上帝的旗幟批判種族替換階級之後的種種不公,卻難以回答他所率領的民權團體中女性地位低下甚至遭到刻意忽視的現象。
而這只是烏托邦的夢想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之一,當無孔不入的政治正確開始乾涉民眾的自由意志,這種難以自洽的邏輯矛盾反而顯得尖銳起來。
烏托邦試圖安排每個個體的命運,而擊碎烏托邦的則是那些成為變數的小人物,從《重裝任務》到《飢餓遊戲》,撕開溫情和虛偽的無一不是那些原本的秩序服從者。
比如狐狸尼克。
狐狸尼克的姓氏是王爾德,也就是那位英國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毒舌詩人。王爾德的玩世不恭及其對於悲涼情結的情有獨鍾同時構成了狐狸尼克的自我屬性,他的結局更是響應了王爾德的名句:“我們都生活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王爾德在英國的墓碑上遍布著前來弔唁的女性獻上的唇印
兔子茱蒂和狐狸尼克擁有相似的童年陰影,只不過前者因而更加堅定了信念,後者則沒能獲得與偏見抗衡的勇氣。也正是基於這種差異,兔子茱蒂在《動物方城市》的劇情推進當中起到的是動力作用,沒有她的堅持和執著就沒有真相的水落石出,但是狐狸尼克則趨近於“關鍵先生”的角色,是他通過樹獺查到了大先生的線索,是他帶著差點就被革職的兔子茱蒂繼續查案,是他想到藉由交通監控尋找黑豹的下落,也是他消融了來自兔子茱蒂的無心傷害決意幫助後者完成使命。
而狐狸尼克之所以能夠做到兔子茱蒂空有一腔熱血卻無法辦到的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在“破罐子破摔”的成長歲月裡始終混跡於社會的夾縫裡,他比熱愛這座城市的兔子茱蒂超出百倍的熟悉這座城市,所以他也是整場陰謀裡唯一一個置身事外的失控者。
這只習慣半睜雙眼、永遠一副懶洋洋的神情的狐狸,才是《動物方城市》迷倒眾生的靈魂。至於他和兔子茱蒂的“反差萌”,同樣可以用王爾德的俏皮語錄來做出精闢的評價:“任何人都能對朋友的不幸感到同情,但要消受一個春風得意的朋友,則需要非常優良的天性。”
彷彿聽到了狐狸無奈的笑聲。
一個事實:學不會的美國動畫工業
《動物方城市》的最大優點在於:觀眾其實毋須了解上面贅述的那些隱喻和背景,在抽離這些彩蛋式的文化景觀和寓教於樂之後,這部電影的流暢度和出彩度依然逼近滿分,足夠感染全年齡段的受眾。
這也是迪士尼引以為傲的“生造IP”的本事,不需要冗餘的內容鋪墊和多次變現,一部作品即可奠定一條吸金不斷的商業鏈條。
美式動畫與日式動畫作為ACG產業的兩極,分別代表工業模式與工匠模式的極致。
儘管斯坦·李被譽為是超級漫畫英雄之父—X戰警、蜘蛛俠、綠巨人、神奇四俠均為他的創作—但是真正影響那些動漫形象的,是版權採購方僱傭的各個編劇,在美國推崇的市場競爭中,世界觀的分裂幾近平常,不同編劇締造不同宇宙的情況每天都在上演,哪個宇宙受到讀者的歡迎,那個宇宙的故事就會更加“正統”,亦更具商業價值。
與美國的流水線叢林不同,日本講究創作者從一而終的主導,像《死亡筆記》這樣由編劇與畫家合作產生的作品實屬少數,而畫家執筆之外的同人作品很難形成版權。於是,日本的動畫產業對於IP的依賴更加嚴重,一部漫畫作品只由經過動畫化、電影化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回報,反過來講,沒有IP的基礎,很少有製片公司敢於獨立推出動畫電影。
中國動畫電影長年游離於美國和日本之間,既垂涎美國大片生產機器的轟鳴,又鍾情日本作坊所具備的低成本和低風險,於是,《西遊記》這個免費的IP一再遭到濫用,卻始終缺少本土動畫的代表之作。
《動物方城市》的創作過程十分曲折,在迪士尼原本的計劃當中,這部電影的劇情有些類似《飆風雷哥》這樣的公路及江湖色彩,狐狸尼克是一個被捲入陰謀的逃犯,而兔子茱蒂則是奉命捕捉他的明星警探,在這個設定裡,狐狸尼克有著雄心壯志,而兔子茱蒂則功夫一流。

《動物方城市》的早期草稿
受僱於迪士尼的本片編劇菲爾·約翰斯頓—他也是《無敵破壞王》的編劇—堅持將劇本修改得更加貼近現實,並力主引入那些纏繞著美國人心頭的陰霾:藕斷絲連的種族問題、備受質疑的美國精神等。
在傳統的勞資模型裡,這種“夾帶私貨”的偏執很容易被視作冒犯和僭越,但是美國編劇的地位—以及美國編劇協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的後盾勢力—保障了他們有權決定一部影視作品的生殺大權,《動物方城市》也是在多次磨合之後才有了現在的優秀模樣。
另一方面,好萊塢的編劇也遵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遊戲規則,只要狀態不行或是創作遇到障礙馬上就能找到替換的人選,這種流動性固然有些不近人情的殘酷,卻保證了整體力量的均衡,或者換句話說,好萊塢樂於用高薪去武裝編劇,但從不締造大師,沒有哪個編劇可以依靠名聲保住飯碗。
這在日本包括中國的同行看來實在難以效仿,尤其是宮崎駿這樣的造神運動已經為市場釀造出了難以否認的榜樣之後,再去轉換觀念在大師面前談論資本無疑就有些過於充斥著腐蝕性和侮辱性了。
以意外創造票房神話的中國動畫電影《大聖歸來》為例,在中國市場的想像空間內,一個受到尊敬的藝術創作者必然有著苦行僧式的形象,最好是傾其一生的結晶傾囊澆灌於旨在傳世的作品上,這位大師不僅大隱隱於市,而且最好是視金錢如糞土,堅持所謂創作的獨立性,憤慨於行業里外的“圈錢”行徑並與之保持距離…
只要這樣的期許一天存在,中國的動畫電影產業就一天無法從部落文明走入城邦文明。
以及…
羅傑·伊伯特—美國最負盛名的影評家之一—在部落格上無可奈何地感慨“電影產業猝死”,惋惜在影片和家庭觀影面前傳統電影如同打字機和留聲機一樣流落在時代之後。
這就是美國知識分子們普遍的憂患精神。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教育、網路、文化產業、電影工業以及民主制度,學界卻始終充斥著對一切現狀的批判和對未來的憂慮。正是這種幾乎苛刻的從未滿足的挑剔精神,才能讓高嶺之巔始終繁花盛開,每每驚艷。
對真正的強者而言,超越自己的只能是自己。第一步,就是對自己舉起解剖刀。
《網易(NetEase, NTES-US)科技》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