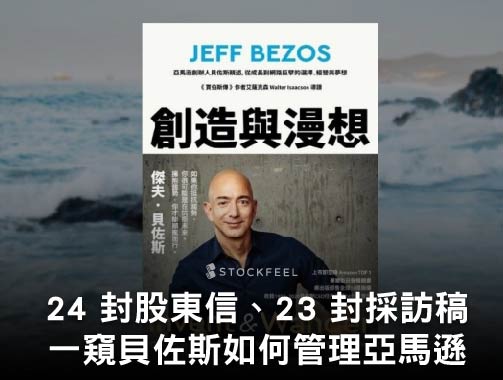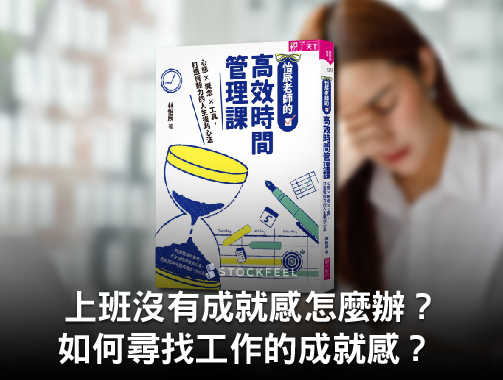2021 年初,我的學業進入了一個死循環。我是芝加哥大學高分子化學和免疫學交叉領域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使用合成方法為疫苗和基因遞送設計出更安全、有效的材料。雖然我剛讀研究生的產量很高,但長時間的埋頭工作已經不再能轉化為實驗成果,我對於實現人生目標感到無望。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我開始尋找出現瓶頸的原因,然後發現我在實驗室裡的「安靜時間」其實一點也不安靜,比如在做色譜柱或顯微鏡實驗時,我本來應該靜下心思考科學問題,但我卻在看影片、刷手機。雖然我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把效率補回來,但我的工作看起來雜亂無章,很沒條理。我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但工作效率卻越來越低了。在實驗室忙到很晚回家後,我還要利用晚餐時間或在床上回信件和Slack上的消息。長期累積的問題終於在去年夏天爆發,當時,無法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我不得不向學校的心理健康服務尋求幫助。
經過心理輔導和個人反思,我終於意識到了我的問題所在:我得了手機成癮症。
沉迷機制
這種情況不只我一個人有。科技公司的一些離職員工,比如已經離開Google的Tristan Harris和已經離開Facebook的Frances Haugen,都公開談論過那些讓用戶不能自拔的社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算法。這些App使用與角子老虎機相同的獎賞機制,通過無法預測、令人上癮的獎賞程式和熱度排名,掠奪用戶的注意力。研究顯示,美國民眾平均每天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超過 3 小時,使用手機對大學生的激勵作用也已超過了食物。
為了奪回被搶走的注意力,我決定減少與外界的互動,工作時只使用一個不連網的基本款手機,當我用回智慧型手機時,我把上面沒用的App都刪除了。我開始用iPod聽音樂,把發送給我的所有資訊都集中到電腦上,或是等我到家了再處理。其他人也嘗試過別的策略,有些人用軟體限制自己的螢幕時間(如今可直接在iOS和安卓系統啟用),有些人選擇改變生活方式,比如日落之後關手機,或是為休息時間安排各種活動,避免自己陷入無意識的刷手機循環(更多方法可參考Cal Newport在 2019 年出版的Digital Minimalism一書)。
有一點很能體現智慧型手機的成癮性質:當我第一次嘗試斬斷這種依賴時,我經歷了戒斷綜合徵,我一整天盯著iPod看,希望它能給我帶來一絲已不再有的多巴胺。但久而久之,我開始利用這些安靜的時間做別的事情。如果實驗過程很長,我就會去看論文,並養成了在休息時間寫文章的習慣。這些行動已經有了成效:目前我正在和導師合作一篇綜述文章,我還寫出了這篇專欄文章和其他個人感悟。我參與會議的積極性提高了,不僅準備更充分,還能提問題和手寫筆記。
精神健康
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我的焦慮減少了,產量和創造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原來混亂不堪的工作與生活關係已經有了清晰的界線,研究思路也更多了。現在,即使我帶著智慧型手機,我也沒有了不停查信件或看資訊的衝動,而是能夠更專注地聚焦手頭的工作。
和改變任何生活方式一樣,改變智慧型手機的使用習慣也會帶來不少問題。有些同事朋友會怪我「失聯」,我也經常錯過WhatsApp和Slack等溝通軟體上的資訊。我現在很少上學術版的LinkedIn和Twitter,我甚至把Twitter整個刪除了,這或許會影響我的職業前景,但在我看來,整個改變是利大於弊,這些犧牲對於樹立界線和提高產量來說不算什麼。
作為科研人員,面對各種分心的雜事時,我們很難管理好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無論處於人生的哪個階段,許多研究生和科研人員都面臨著精神疲勞和心理健康的問題,而新冠疫情讓這種問題更嚴重了。對此,科技至少要負有部分責任。雖然我的家人朋友和科研同事都承認少用手機會有幫助,但很多人告訴我,他們擔心錯過重要資訊,也不敢輕易杜絕社交來往。
如果你發現自己也陷入了這種情況,我鼓勵你至少思考一下,你願意讓手機在多大程度上干擾你的日常工作。為自己留出按下暫停鍵和不受打擾的時間,對抗智慧型手機和現代科技帶來的數位噪音。在這百年一遇的疫情中,這將是我們作為科學家和普通人的製勝法寶。
參考文獻:
- Alter, A. Irresistible: The Rise of Addi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Business of Keeping Us Hooked (Penguin, 2017 ).
- Bhargava, V. & Velasquez, M. Bus. Ethics Q. 31 , 321 – 359 ( 2021 ).
- O’Donnell, S. & Epstein, LH Addict. Behav. 90 , 124 – 133 ( 2019 ).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