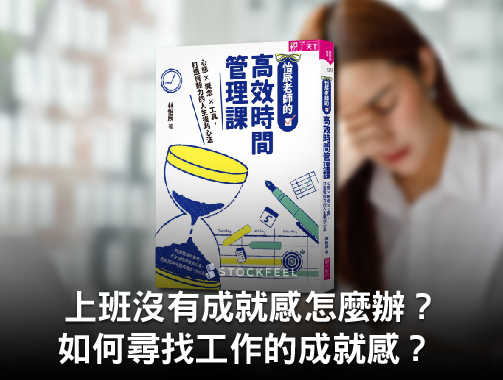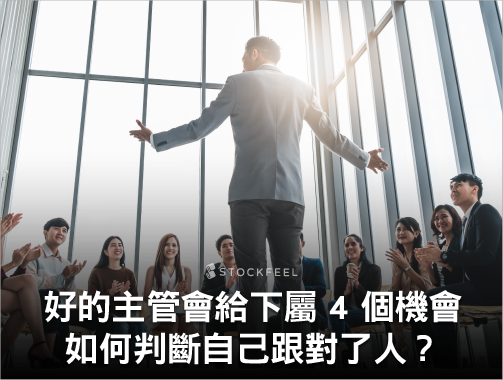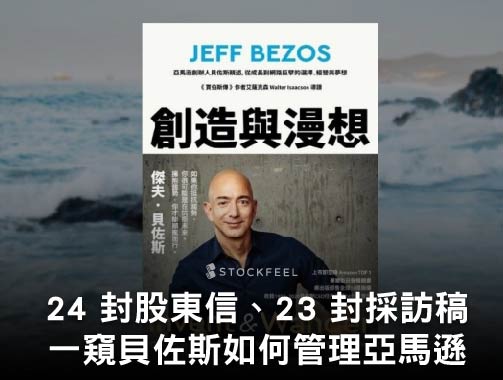當代人對待 “ 忙碌 ” 這件事情的態度,總是有點口是心非。我們對忙碌這件事,儼然陷入了一種又愛又恨的態度:它蠶食了我們的精神生活,但我們又確實能從中獲益,在當下的語境裡,它正在逐漸演變成 “ 一種有價值的痛苦 ” 的代名詞。

▲《助理》, 2019
與此相對的,關於 “ 自由職業/自我僱傭 ” “ 提前退休 ” 的討論和爭議也一直都在:摸魚當然是開心的,但徹底的清閒,似乎並沒有它看上去那麼歲月靜好,因為我們已經很難坦然地享受無所事事。在忙碌和清閒之間,在時間的轉讓和擁有之間,為何仍有焦慮在一以貫之?
“ 忙碌令我快樂 ” ,真的嗎?
漢語的博大精深,從 “ 忙 ” 這個詞就能體現。當我們說別人 “ 忙 ” 的時候,往往會積極化這個詞的內涵,比如所謂的 “ 大忙人 ” (言下之意是對方被很多人和事所需要);而當主語是自己時, “ 我很忙 ” 又總是傳達著焦急或者疲勞之類的負面情緒——這既是忙碌在語言層面的複雜性,也間接說明,忙碌的是自己還是別人,會影響到我們到底能不能客觀看待這件事。
事實上,人類並不天生反忙碌,尤其是主動忙碌。早在 2017 年,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授 Silvia Bellezza 就透過一系列實驗,得出一個現在看來簡直稀鬆平常的結論:對當代人來說, “ 看起來很忙 ” 已經成為了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人們總是將 “ being busy ” 和一些優秀的特質相關聯,比如進取、堅毅、野心等等被認為在職場十分稀缺的好品質。
換句話說,看到那些在高鐵飛機上一直帶著耳機聊工作、隨時拿出電腦就開工的人,我們在感嘆一句 “ 他可真忙 ” 之餘,往往也會習慣性地判定,嗯,這人應該是混得不錯。有研究認為,如果是從個人主觀意願出發的 “ 不想閒著 ” ,確實可能會調節負面情緒、強化自我認知,進而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也就是說,雖然人們總是在社交媒體上抱怨自己的生活被工作霸占了,但其中應該也有一部分人,實際上想表達的是 “ 我存在,而且我很重要 ” 。
這就是為什麼直到現在,如何進行時間管理(或者用更入時的說法,multi-tasking)、合理規劃,如何利用有限的時間完成最多的任務,依然是當代人對自己能力的證明(儘管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這種能力)。劍橋大學人類學家詹姆斯·蘇曼耶也在《工作的意義:從史前到未來的人類變革》裡說,只要聚集在城市裡,我們就無法把工作當成簡單的謀生手段,而是擁有高度社會化水平和適應能力的證據——這意味著你是一個真正的 “ 社會的人類 ” 。
問題是,既然忙碌如此有益,為什麼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像一些人那樣 “ 享受 ” 忙碌?
答案可能在另一位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那本大名鼎鼎的《BULLSHIT JOBS》裡。David Graeber 在這本書裡就曾經毫不留情地說, “ bullshit jobs ” 其實充斥在人類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為了保證自己不失業,許多人不得不假裝很忙。隨著無益工作的膨脹,哪怕是正常工作也被這類工作的荒誕模式沾染。
如果我們提取某個生活的片段來觀察,會發現這種 “ 被動忙碌 ” 其實無處不在:該忙的時候在開會,不該忙的時候卻要加班,上班要表現出全情投入的模樣,下班還得想方設法營造自己只是暫時離開工位的錯覺,休息日也會發一些主管可見的貼文彰顯自己的工作態度⋯⋯,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當代工作的縮影。

▲《未生》, 2014
當然,還有一種忙碌介於主動忙碌與被動忙碌之間:只要一閒下來就想看點什麼、做點什麼、知道點什麼,哪怕只是 “ 沒用的知識又增加了 ” 。畢竟,忙碌給人帶來成就感,時間就是金錢,自我充電、自我進步、自我驅動,即使你其實並無真正想做的事。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不敢閒下來?
相對於成功人士是如何白手起家或者奮鬥終生,這幾年,那些逃離都市、追求慢生活、提前開始養老的故事,作為 “ 主動選擇無事可做 ” 的當代生活樣板明顯受歡迎了起來——在收入有保證的前提下。很明顯,我們對忙和閒的偏好之中,不可避免地摻雜進了一些別的考量。我們總是在這個時代看到那些不上班的人、隱居的人、去過真正的日子的人,羨慕和幻想所謂這樣的生活當中說走就走的那部分,但卻抗拒和不願承認它也有收入不穩定、朝不保夕的那部分。畢竟類似的狀況換一句話說就是家裡蹲、啃老,年輕人早已被這些話術鞭笞著遠離清閒。

▲《高年級實習生》, 2015
如果忙碌是有價值的痛苦,那麼清閒就是可引起焦慮的自由。在當下,越來越多人患 “ 空白時間焦慮症 ” ,只要一閒下來就會覺得自己沒有在學東西,進而否定自我存在的價值。但這個認知並不表示我們可以立即投入主動忙碌中,絕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不停點亮手機螢幕,點開冷清的社交 app 再退出,在碎片化的資訊中消磨掉空白的時間。
我們無法接受過分忙碌,但也不代表就想過得太過清閒(尤其是毫無存在感的清閒)。在被動忙碌的時候,我們大可以說是工作、資本、生活令我不得不連軸轉,但當選擇權交付到自己手上,終於擁有了自己的時間,但還是不知道想做或者可以做什麼的時候,才是真正拷問我們的自由意志的時刻。
這種狀態,和堪稱當代人均迷思的 “ 什麼是做自己 ” ,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謀而合的。大多數人頂多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不要枯燥的重複勞動、不要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不要在經濟上精神上依附他人、不要被系統控制,但如果真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麼,想做什麼樣的人,單身還是結婚、打工還是求學、種地還是上天,以及可能會為此而面對什麼,才是真正的困難。畢竟,生活是有慣性的,而跟著慣性走總是舒適的。
生活的盡頭,是摸魚嗎?
在越來越密的當代生活裡,日益完善的永不離線式工作文化讓我們的私人空間被不斷蠶食,年輕人將工作視為一種 “ 不得不忍受 ” 的禁錮,職業的發展已經不再被看成是努力就有收穫的等價交換,於是他們紛紛做出 “ 非關鍵時刻拒絕再卷 ” 的決定,試圖從被動忙碌當中脫身,用死線之前的頑強摸魚幫自己找回一點有控制感的悠閒。
摸魚哲學不動聲色地成為了新型職場正義,它的誘惑在於它的忙裡偷閒、苦中作樂,所以哪怕有時候我們雖然已經在休息了,但還是在一刻不停地劃手機,堪稱偷閒中的偷閒。但遺憾的是,即使是休息,想要高品質的娛樂和休閒,其實一樣是需要思考的,而摸魚不需要思考,只用一些簡單的手指動作,便能獲得瞬時而同質的快樂。所以摸魚只是一種瞬時體驗,而不負責解決任何根本問題,因為它像我們厭惡忙碌又難耐清閒一樣,只是以一種抗拒的姿態聲明自己 “ 不想要什麼 ” ,但不能給出建設性的回答。

▲《辦公室的故事》, 1977
“ 不想工作,只想養老 ” 、“ 為了退休而工作 ” 的聲音層出不窮,與前幾代人相比,這屆年輕人早早開始考慮起了養老問題,迫切進入退休生活。在忙碌和清閒之間搖擺不定的年輕人,需要回答的是有關時間的失與得的問題。如果忙碌已經成為當下不得不為之的生存本能,那麼摸魚則更像是一邊抵抗職場內捲,一邊掩蓋自己始終找不到彼岸的焦慮的混合物。在越來越密不透風的當代生活裡,忙碌被視為洪水猛獸並不奇怪,只是清閒看似平易近人,若想接住它卻需要十足的清醒與堅定——如果我們認同 “ 行動才是構成一個人之為人的基礎 ” ,那麼,我們對忙碌的糾結態度,就還會永遠持續下去。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