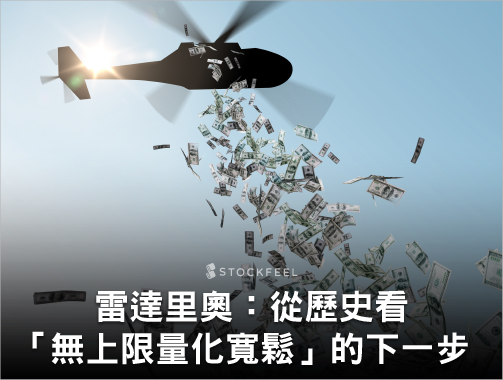羅馬並非一日造成,現代 央行 的 政策 角色 也經歷幾多演變,從扮演政府的銀行,至銀行的銀行與最後貸款者的角色,甚至在危機期間,若干主要央行進一步轉為最後購買者,並充當信用配置者。央行的目標隨著當時經濟狀況與政策需求而演變,不僅包含物價穩定、金融穩定,甚至危機期間協助融通需求,更隱性地追求經濟成長。觀察近代以來央行職能演變與典範轉移,如同搭時光機上了一門實務的貨幣銀行學與總經發展史。
伴隨政治、經濟與金融環境的轉變,國際間中央銀行(以下簡稱央行)角色亦不斷演變,全球金融危機前,由最初扮演較為全能的角色,逐漸縮小至僅聚焦於維持物價穩定;迨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央行職能又再度擴張至強調金融穩定的重要性,近期的武漢肺炎(COVID-19)危機,更使央行角色進一步擴大至促進就業與總體經濟穩定。
近年來,央行為了因應危機所執行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與信用政策(Credit Policy),使央行直接介入的金融市場與經濟活動層面更深也更廣,也從而擁有了更廣泛的影響力;在此情況下,央行職責、與其他政策工具的搭配,以及有關央行獨立性(Independence)等議題,已引發各界熱議。
一、全球金融危機前央行角色的演變
回顧歷史,從央行的緣起來看,央行主要擔負政府的銀行(代理國庫收支)與銀行的銀行(銀行關係網絡與支付系統的核心)的角色,其後並成為市場流動性的最終提供者,也就是最後貸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
這段期間央行的主要功能有:物價穩定、金融穩定,以及危機時期協助政府與民間的融通需求,但在承平時期,對政府過度濫用財政予以規範。儘管許多央行當初成立是為了協助提供戰爭的資金來源,但承平時期,央行在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的取捨,隨時間不斷演變,則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此外,全球金融危機前,具有高度獨立性的央行較易維持物價穩定,以及資產價格泡沫較不宜以利率工具來積極因應,可謂這時期對於央行角色的重要看法。
(一)1840 年代以迄於全球金融危機前,對央行角色看法的演變
曾任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 BoE)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的 Charles Goodhart,依循歷史軌跡,將有關央行角色的重要看法概略分為三階段:
1840年代 ~ 1914 年代
依據實質票據學說(Real Bills Doctrine),只要央行的貼現與借款都與實際的產出與交易所衍生的票據有關,則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可同時達成。因為這時期的央行除了作為政府與銀行的銀行,兼營一般商業銀行業務是常態,扮演較為全功能型的角色;這項針對央行貼現與借款的條件較易成立,因此也就提高兼顧物價與金融穩定的可能性。
同時,對於作為最後貸款者的央行而言,其應僅向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金融機構提供融通,並且應施以比較高的懲罰性利率。此一由巴治荷(Walter Bagehot)在其1873年出版的《倫巴底街》(Lombard Street)書中指出的央行角色,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
1930 年代 ~ 1960 年代末期
1930 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與金本位制度崩潰,對於各國央行是一大挫折;且因二次世界大戰,政府須直接分配資源控制需求,不再依賴價格機制,政府乃接管貨幣政策的決策,央行在國內政策上,僅扮演類似顧問諮詢的角色。
此外,1929 ~ 1933 年的金融體系崩解,讓各界咸認金融體系內的過度競爭,不利於維持金融穩定,因而採高度的金融管制。雖然管制造成銀行倒閉家數在 1930 年代之後相對稀少,但也使得當時的央行相對欠缺維持金融穩定的經驗。
1980 年代 ~ 2007 年
這是一個資訊科技進步伴隨著市場開放與競爭程度上升的階段,解放了二戰以來備受拘束的金融體系,國際金融市場也因之蓬勃發展。尤以歐洲美元市場的發展,深深改變了銀行業的本質與架構。銀行不再受限於散戶的存款與自身所持有的流動性資產,可透過批發市場取得融資,擴大自身的放款能量。
這些變化一方面導致利率的波動加大,以及貨幣數量與所得、通膨等總體變數的關係變得不穩定,使得國際上主要央行紛紛放棄貨幣目標化(Monetary Targeting)機制,並陸續轉向通膨目標化(Inflation Targeting)機制,以穩定物價為首要目標。另一方面也在銀行業的競爭加劇下,導致金融體系的風險日益明顯,進而促成國際間的監理制度改革,陸續推出Basel I、Basel II,提高對銀行自有資本的提列要求。
整體而言,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一般咸認央行以調整短期利率達成法定的通膨目標,是近乎完美的貨幣政策執行策略;然而,全球金融危機引發對於通膨目標化機制的質疑,認為央行當時用以達成物價穩定的操作方式,不足以確保金融穩定。
(二)央行獨立性與物價穩定
1964 ~ 1982 年的大通膨(Great Inflation)時期,是全球央行日後專注於物價穩定的重要關鍵。1964 年,美國的通膨率僅略高於1%,但歷經兩次能源危機與越戰、Fed 貨幣政策被迫與擴張性財政政策協調;再加上就業極大化的法定目標,Fed不得不續採寬鬆性貨幣政策。這使得物價不斷上升,至 1980 年美國的通膨率已高達 14%。隨後,在各界普遍意識到高通膨帶來的龐大社會成本,Fed 才得以專心致力對抗通膨,尤以前 Fed 主席 Paul Volcker 不惜以大幅升息來擊退通膨,始將通膨率回降至約 3%,進而開啟其後經濟溫和成長與物價穩定的大溫和(Great Moderation)時代。
1970 年代的高通膨經驗賦予央行獨立性的理論基礎。當時決策官員相信,失業率與通膨間有穩定的抵換關係,貨幣政策若以稍高的通膨為代價,可達成較高的就業。然而,此類政策有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的問題。當貨幣當局信守控制通膨的承諾失去可信度(Credibility),將導致就業與通膨間的抵換關係消失。
為了克服時間不一致的問題,央行需展現達成物價穩定的決心,以重新獲得可信度;為此,央行需承諾不採恐引發通膨的政策路線,同時抗拒任何來自政府要求追求物價穩定以外目標的政治壓力。社會亦逐漸走向讓央行得以不受短期政治壓力,並賦予央行獨立性的架構。這普遍的共識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物價穩定是共通的目標,但實現此一目標有賴合適的貨幣政策架構。
此一架構包含三項特徵:(1)物價穩定是央行須達成的法定目標;(2)在央行可使用的工具外,央行需具備高度獨立性;(3)貨幣政策架構須包括具效力的權責化(Accountability)與透明化(Transparency)要求,讓央行得以解釋其決策如何達成其目標。此一架構係向大眾保證,獨立性高的央行不會濫用權力。
1990 年代與 2000 年初期間,此一貨幣政策架構實施情況良好,各界普遍認為,具備獨立性的央行,並使用單一工具─政策利率,得以成功讓通膨與通膨預期獲得控制;跨國的研究亦顯示,獨立性與 OECD 國家的通膨具有負向關係。此外,央行獨立性亦為帶來產出與通膨的波動度降低之關鍵因素,1980 年代中期以來,實質產出成長率的變動度下降一半,而通膨的變動度下降約 2/3,此即為前文已提及的大溫和時期。
(三)面對資產價格泡沫,不宜以貨幣政策採預防性措施
全球金融危機前,在央行界與學術圈有所謂的「傑克森霍爾共識」(Jackson Hole Consensus),亦即貨幣政策僅應以物價穩定為目標,貨幣當局不應試圖對資產價格泡沫預先採因應措施,因為主動戳破資產價格泡沫會導致不可預期的後果,甚或引發金融不穩定。例如,美國曾於 1928 ~ 1929 年,以及日本於 1989 年,均曾為抑制資產價格暴漲而緊縮貨幣政策,卻分別導致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以及日本經濟陷入長期通縮。
學術界的研究,如 Ben Bernanke 及 Mark Gertler 的相關研究亦指出,在辨識泡沫這件事上,央行並未較市場擁有資訊上的優勢。此外,貨幣政策若對泡沫做出回應,而非積極對於預期通膨做出反應,反而會導致產出與通膨的波動加劇。當時主流觀點咸認,等待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後,央行可透過貨幣政策或扮演最後貸款者的角色,抑制泡沫破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1990 年代至 2000 年初的黃金時期,以「物價穩定」為核心的政策架構實施良好,央行獨立性明確,使用單一政策工具――政策利率成功控制通膨預期,全球經濟享受了「大溫和時期」(Great Moderation)。
二、全球金融危機後央行職責不斷擴大
銀行業(尤其是影子銀行)透過貸款或資產證券化、短天期的批發市場大量籌資,規避金融監理,最終釀成2007年的次貸危機,並擴大成全球金融危機。危機過後,央行家與學者反思,物價穩定恐無法保證金融穩定,亦無法確保經濟繁榮;過分強調對抗通膨,讓央行忽略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放任資產價格膨脹,易肇致金融危機。
央行從中學到的教訓是,除了物價穩定,也必須關注信用擴張與資產價格波動,許多央行因此再度將金融穩定納入職責;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COVID-19危機期間,央行為提振經濟,大採非傳統性貨幣政策,跨越傳統上與其他機構權責的分際,似又再度回歸到較為全能的角色。
(一)全球金融危機後,突顯金融穩定的重要性,若干央行再度將金融穩定納入職責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央行家與學者反思過去大溫和時期只要維持物價穩定,即可確保金融穩定的主流思維,以及被廣泛採行的通膨目標化機制;處於危機核心的已開發國家,因過度專注於物價穩定,致坐視擔保品價值高估以及信用快速擴張的風險。於是,若干央行已將金融穩定納入職權範圍內,包括英國、俄羅斯及愛爾蘭在內等 14 個國家的央行,擴大金融監理的參與程度,掌管總體審慎工具(Macroprudential Tools),俾解決涉及金融穩定的問題;例如,1997 年,英國一度將金融監理的職責,由 BoE 移轉至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但鑑於 FSA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監理不力,2013 年英國將金融監理權再度移回 BoE。
此外,許多主要央行即使未將金融穩定充當正式的貨幣政策目標,但如美國 Fed 主席 Jerome Powell 也曾表示,有責任與其他機關一同促進金融穩定,並將金融穩定職責,與維持物價穩定、追求就業極大化這兩大法定職責,視為具有高度互補性。
(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尤其肺炎危機期間,央行角色進一步擴大至高風險的信用分配領域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為挽救經濟,主要央行的政策工具箱已大幅擴增(比如資產購買計畫及融資機制等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引發侵入財政政策、信用分配領域的疑慮。
迨至近期,COVID-19 疫情爆發所致的大封鎖(Great Lockdown),業已引起突發性且廣泛性的經濟活動停擺,對各國景氣衝擊快速且巨大,致主要央行更進一步採行較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之規模更大且更「非傳統」的寬鬆措施。主要央行更直接介入特定信用市場,透過銀行,甚或是進入初級市場、次級市場購買包括公司債、股票、ETF 等私部門資產,對大企業、中小企業及地方政府提供信用支持。
當前的央行又再度肩負諸多任務,所扮演的角色進一步擴大,由最後貸款者,轉為最後購買者(Buyer of Last Resort),並充當信用配置者(Credit Allocator);這除了承擔部分財政當局的紓困責任,還兼任類似於商業銀行的角色,向特定群體提供資金。此一發展,引發外界憂心;前Fed副主席、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Alan Blinder就認為,雖然Fed等央行聲稱因應危機所採措施,是貸款工具(Lending Tools),而非支出工具(Spending tools),惟若這些所謂的「貸款」無法被完全償還,央行恐是跨越職責的紅線。
最末,誠如Fed主席Jerome Powell在本(2020)年5月底的一場由普林斯頓大學主辦的視訊對談中表示,Fed“跨越了許多以前從未碰觸過的紅線。”他補充說,儘管存在風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先放手做,再想後果。」(This is that situation in which you do that, and you figure it out afterward.)。有論者認為,這後果是央行的主要政策目標,已從維持物價穩定,兼顧金融穩定,乃至於正隱性地同時追求經濟成長,並不惜動用任何政策工具來達成,也就是央行的角色再次大幅位移。
《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清除絆腳石-_-.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