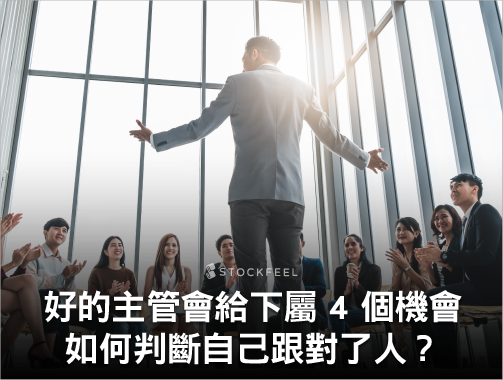2019 年,美國曝出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醜聞。聯邦檢察官在 3 月對 50 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員、商業領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賄(金額從 5 萬~120 萬美元不等),為子女 “ 購買 ” 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學資格。輿論嘩然,美國兩黨政要也紛紛對其予以譴責。
公眾的憤怒無須解釋,因為這踐踏了美國人深信不疑的 “ 菁英主義 ” 理想或 “ 菁英制 ”(meritocracy)原則:社會與經濟的獎賞應當依據才能、努力和成就這些 “ 績優 ”(merit)來決定。人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成績優異者獲勝。因此,最好的大學應當錄取成績最出色的學生,收入最高的職位應當留給最有能力的人才。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不容挑戰的理想原則。其實,不只是美國人,包括我們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現代社會都認同菁英制,認為 “ 擇優錄取 ” 及 “ 能者多得 ” 是理所當然的公平原則。

可是,近來有學者向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發起挑戰。先是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在新書《菁英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評論說,人們對招生醜聞的譴責完全正當,但並沒有觸及深層的問題,他們只看到有人破壞遊戲規則,卻沒有看透這個遊戲本身是一個陷阱。他認為,現在 “ 美國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為菁英制沒得到充分落實,而是菁英制本身造成的 ”。菁英制根本無法兌現它許諾的公平競爭與社會階層流動,在虛假承諾的偽裝下只是一個陷阱。
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也加入了對菁英制的討論。他在 2018 年 5 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已明確指出 “ 菁英制的傲慢引發了美國社會的分化 ”,促進了民粹主義的興起。他在 2019 年秋開設了一門 “ 菁英至上論及其批評者 ” 的本科生研討課,並曾邀請馬科維茨到課堂上與學生討論。2020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著作《精英的傲慢》。
桑德爾早年因其對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正義論》的批評而蜚聲學界,堅持批判自由主義的個人觀,被視為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這部著作是其社群主義視野的最新延伸。他論證的主要觀點是,菁英制造成了一種 “ 暴政 ”,讓社會撕裂、背離正義,也讓工作喪失了尊嚴。
在這本書的開篇,桑德爾也提到了近年來美國大學招生錄取的醜聞,但他隨即表示:“ 大學招生錄取並不是爭論的唯一場合。在當代政治中,關於誰應該得到什麽的辯論比比皆是。從表面上看,這些辯論關乎公平:每個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機會去競爭理想的商品和社會地位嗎?但我們關於價值的分歧不僅僅涉及公平。這些分歧也涉及我們如何定義成功和失敗、贏和輸——還關於成功者對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應該持有什麽態度。”
” 大學招生錄取 ” 就是菁英制的表現形式之一。菁英主義倫理的核心是,成功是憑自己的努力和奮鬥可以獲得的東西、“ 英雄不問出處 ”,哪怕你出身貧賤,“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如果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那麽成功者就應該獲得獎賞。菁英主義其實本來蘊含著一種打破固定階層、讓社會流動的許諾,但現實情況是,它最終沒有實現它所許諾的理想。
作為哲學家,桑德爾從道德哲學思考出發,揭示了菁英制的不公平性:影響我們成功與否的因素大都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例如性別、種族、地區、健康狀況、天賦、家庭背景等,這些 “ 運氣 ” 和你自己其實沒有什麽關係,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你是否能進入大學、能讀什麽樣的大學,進而影響你未來的事業發展。
若我們的命運如此深刻地依賴於我們無法選擇的運氣,那麽我們獲得的成就是我們理所當然獲得的嗎?桑德爾援引羅爾斯的觀點,認為運氣在道德上是一個 “ 任意 ” 的因素,因此依賴運氣取得的 “ 菁英 ”,並沒有道德上 “ 應得 ” 的正當性,那麽憑借 “ 菁英 ” 獲得的社會等級也就談不上公平。
對菁英制度的批判
馬科維茨和桑德爾等學者對菁英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了:
一、菁英制固化了社會階層,折斷了人們向上攀登的階梯,實際上造就了新的世襲制。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為菁英主義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於打破凝固的世襲階層,讓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憑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獨立宣言》中的 “ 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是所謂的 “ 美國夢 ” 的感召力所在。美國社會的現狀是, 精英階層能夠將優越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代際傳遞”給自己的子女。這當然不能依靠被廢棄的世襲制度,而是通過教育。
教育本來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關鍵通道,但優質教育是稀缺資源,需要競爭才能獲得。爭奪優質教育資源是一個全球現象,在亞洲是如此(想想電視劇《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歡喜》中的情景,還有 “ 小學不讀民辦,大學就讀民辦 ” 之類的廣告),在美國也不例外。
無數家庭卷入膠著的戰場,但精英階層最終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這突出體現在著名高校學生的家庭階層分布。桑德爾指出,在常春藤聯盟高校中,來自金字塔頂端 1% 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底層 50% 家庭的學生加總還多。目前在貧富學生之間的學業成績差距,已超過 20 世紀 50 年代黑人與白人學生之間的差距。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耶魯大學校長小金曼.布魯斯特就曾明確主張,學校要根據學生的成績而不是其家庭背景來錄取學生,希望由此打破精英世襲。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為精英階層找到了保持優勢的秘訣:通過支付高額費用,讓孩子獲得最好的升學訓練,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種昂貴的課外補習班和培訓項目,讓他們的子女在各級入學申請中獲得難以匹敵的競爭力。頂層富裕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是驚人的,對每個孩子的累積花費可以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由此 “ 維護了一個有效的世襲統治階層 ”。
第二,推行菁英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結果瓦解了中產階級。由於工作職位和收入水平與教育水平密切關聯,可想而知,菁英制會導致精英階層與中產階級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曾是全世界最主張平等主義的社會,托克維爾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 1% 人口的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占比,當時在美國不到 10%(而在英國超過了 20%),但現在上升到 20%。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企業高管的平均工資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資的 20 倍,而現在達到 360 倍。貧富差異的加劇帶來了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整個中產階級在過去半個世紀內不斷衰落,小部分進入上層和精英階層,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斷下降(這也使中產階級與底層人口的貧富差距相對緩和),結果形成了頂層與中下層之間嚴重的兩極分化。一個由中產階級占據美國主導地位的 “ 橄欖型社會 ” 消失了。
桑德爾認為,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辜負了所宣稱的菁英主義原則,而是這種理想主義的思維本身就有缺陷。菁英主義侵蝕著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導致了勝利者的傲慢和失敗者的屈辱。它鼓勵成功者深深沈迷於自己的成功,以至於忘掉了一路上幫助他們的時機和好運,同時也導致他們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資格的人。結果,菁英制助長階級之間的對抗和怨恨,這種社會分裂的狀況會侵蝕西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推動力。
如何擺脫菁英主義的陷阱?
那麽,我們該如何擺脫菁英主義的陷阱呢?桑德爾建議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個方面:大學的角色、工作的尊嚴及成功的意義。
首先,重新評估大學是否應當承擔機會仲裁者的角色。大學文憑是獲得有尊嚴的工作與體面生活的必要條件嗎?在桑德爾看來,這是危險的。我們應通過建立更包容和更開放的教育體制來促進機會平等。他提出了一個創新的方案:讓所有申請者在達到基本學術門檻後,通過抽簽方式來錄取。這種抽簽錄取制,不僅能讓學生減輕壓力,也會減少被錄取學生的優越感。此外,還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幫助沒有文憑,但為社會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們改善生活上。
其次,我們應該更新 “ 工作的尊嚴 ” 的概念,並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爾認為,“ 一個社會表彰和獎勵工作的方式是其定義公共利益的核心 ” 。我們應該記住,工作不只是為了謀生,也是對公共利益做貢獻並贏得相應的認可。我們經常假設人們的收入是他們對公共利益所做貢獻的衡量,但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誤解。馬丁路德.金恩在被刺殺前夕給田納西州孟菲斯罷工的清潔工人演講時曾說: “ 清潔工人和醫生一樣重要,如果沒有清潔工,疾病就會蔓延。所有的勞動者都有尊嚴。” 如今的疫情更說明了這一點。它揭示了我們多麽依賴那些經常被我們忽略的勞動者:快遞員、維修工人、雜貨店店員、卡車司機、護士助理、育兒工作者和家庭護理員等。
最後,在成功的意義方面,桑德爾提出應當重新討論菁英的含義。他同意羅爾斯一個觀點,即菁英依賴於運氣這種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對羅爾斯要在分配正義中清除菁英的看法。在桑德爾看來,分配正義可以納入對菁英的考量,但菁英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簡單地根據市場競爭的輸贏,而是要按照對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來界定。比如,為賭徒提供賭場的經營者可能會在市場上獲得更高的收益,他們的收入會比教師或者醫生的更高,但他們具有更高的價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嗎?
如何來衡量他們各自的優績呢?當然, 對於 “ 什麽是公共利益 ”、“ 什麽是真正的貢獻 ”,人們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爾認為,不能因為存在爭議就拒絕嘗試對菁英做出新的闡釋。他呼籲社會開啟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轉變,捫心自問:“ 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我活在一個獎勵才能的社會中,而這才能恰好是我所擁有的?還是只是因為我很幸運而已?” 意識到運氣在生活中的作用會讓我們變得謙卑。這種謙卑精神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驅使我們重新定義成功的觀念,為我們超越菁英制的暴政,走向一種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馬科維茨與桑德爾對菁英制的批判揭示了嚴重的不平等對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引人深思,催人警醒。當然,他們的批評論述也引發了一些爭議。比如,追究菁英制導致不平等的責任或許錯置了指控的對象,因為菁英主義從未承諾結果的平等,促進機會平等和階層流動在邏輯上無法提升結果的平等性。杜克大學榮休教授約翰.斯達頓在網刊 Quillette 發表的評論中指出,即便在一個極端理想的機會平等環境中,天賦才能的差異仍然會在競爭中產生等級差別,無論競爭的目標是什麽。
當然,嚴格的機會平等必須矯正不平等的起點,可以通過補償措施 “ 拉直 ” 扭曲的起跑線。但在每次比賽的起跑線之前,還存在更早的起跑線,而補償的要求總是可以正當地向更早的階段延伸——從大學錄取延伸到幼兒園入學,一直追溯到遺傳天賦這類道德上任意的運氣因素,這會走向類似 “ 運氣均等主義 ” 的道路,主張“ 敏於抱負,鈍於天賦 ”。但我們很可能會發現,“ 抱負 ” 和 “ 努力 ” 等品性也仍與遺傳有關,那麽徹底的補償措施只能走向(被我們姑且稱為) “ 基因平等主義 ” 的絕境,否則嚴格的機會平等仍然無法實現。
改變競爭的目標也只能更換獲勝的人群而不是等級結構本身,在狩獵時代可能是體力(身強力壯)的等級,而在今天的信息技術時代可能是數學才能的等級。矽谷的程序員和公司的裝卸工在 500 年前的等級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種等級來取代另一種終究也無法達成平等的結果。
顯然,競爭是菁英主義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競爭,也只會造成等級差異。我們崇尚菁英制並不是出於平等的理由,而是因為自由與效率。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原則,菁英制有其無可替代的長處: 最有效地發掘、選拔和使用社會最需要的人力資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個社會受益。“ 菁英 ” 的確立當然取決於特定社會的功能需求,其內涵會隨文化和時代而變化。但無論是騎馬射箭、吟詩作畫還是工程設計,一旦被確立為 “ 菁英 ”,就會成為競賽的目標,最終讓特定的擅長者勝出。
桑德爾並不認同運氣均等主義及其分配正義的解決方案。他的批判指向了當前美國社會的目標定位—經濟政策的唯一目標是提高 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但這並不是美國的一貫傳統,而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後才得以確立的。對 GDP 的癡迷並不是 “ 道德上中立 ” 的,因此將市場競爭、經濟增長與收益分配作為最高的社會與政治議程是有待質疑和反思的。
為此, 桑德爾提出 “ 貢獻正義 ” 的概念,這關乎人們贏得社會的承認與尊重的機會,而這種承認與尊重總是伴隨著為他人所需之物和珍視之事做出的貢獻。他指出,從亞里斯多德、美國共和主義傳統到黑格爾和天主教的社會教義,都曾有豐富的貢獻正義的學說,其基本理念是:“ 當我們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並因所做貢獻而贏得同胞尊重的時候, 我們是最完整的人。” 按照這種傳統,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是 “ 被那些與我們共同生活的人需要 ”,而工作的尊嚴在於滿足這一需求。如果這意味著過一種美好的生活,那麽把消費當作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錯誤的。
由此看來,菁英主義的霸權源自資本主義經濟的競爭邏輯和效率最大化原則,這造成了當代西方社會新的危機。但西方社會的傳統不止崇尚單一的資本主義邏輯。對菁英制的討論將重返政治理論家持久爭論的難題:如何應對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自由與平等之間、效率與公平之間、資本主義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的內在張力?尋求兩者調和的努力實際上貫穿於整個現代歷史。當今西方社會再次陷入平衡失調的困境。這個教訓告誡人們:菁英主義無法單獨應對平等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在這兩種核心的現代價值之間,我們無法二擇其一。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