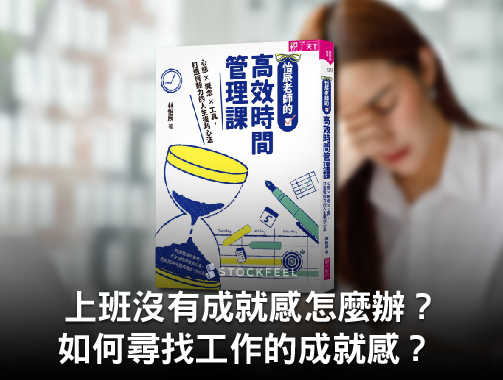據央視新聞報導, 3 月 21 日,東航一架波音(Boeing, BA-US) 737 客機在執行昆明—廣州航班任務時,於梧州上空失聯,目前,已確認該飛機墜毀。機上人員共 132 人,其中旅客 123 人、機組 9 人。中國民航局已啟動應急機制,派出工作組趕赴現場。空難是現代社會最令人揪心的悲劇之一。它與我們日常的出行方式相關,發生頻率低但死亡率高,人生之無常,往往在瞬間。我們希望救援工作一切順利。
今天的這篇文章講述了一個以善後空難為職業的人。空難過後,收拾殘局的工作涉及到各方面,現場遺物清理,DNA 分析比對,通知遇難者家屬並且安排好種種事宜。工作既多且雜,政府和航空公司分身乏術,他們會聘請專門處理緊急事件的公司來協助處理。本文的主人公羅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就職於業內公認最有經驗的一家。
詹森之前在美國政府部門工作, 1998 年加入這家公司之後,經手過多起讓人心碎的空難事故。他尋找墜機殘骸、遺體,識別散落的個人物品,然後將它們如數歸還家屬。對家屬而言,再小的一塊碎片都能帶來莫大的安慰。詹森時常提醒後來的同事,在處理這類事件時,不論多難,都不能代入個人感情。他絕對不會和遇難者家屬有過多聯繫,因為這會讓他覺得自己是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
這份工作是痛苦的。還原物品,像還原一個人在世界上生存過的痕跡。 “ 當你識別私人物品時,你得全各方面了解這些人。他們的播放列表裡有什麼歌?你不是真的要關注他的播放列表都有什麼歌,而是要對比他們的電腦上的列表,看看能不能確認這是誰。 ” 私人物品也是有感情的。當你看到遇難者前幾週剛拍的結婚照時,你無法做到不同情遇難者。但這也正是這份工作的意義,它記錄了一個遭遇悲劇的人曾經如此鮮活,曾被愛過。
再小的碎片也是莫大的安慰
一隊人馬在叢林中跌跌撞撞,砍出了一條能勉強前進的路。他們不清楚自己前進的方向是否正確,也不知道前方會發現什麼。幾天前,偵察機在安第斯山脈上空發現了失事直升機的殘骸,零星地分布在布滿巖石的陡峭山坡上。要想從空中對殘骸進行勘察幾乎不太可能,所以他們需要步行抵達失事地點進行搜尋。
隊伍在灌木叢中步履艱難地走著,帶領他們的是一個身材魁梧的高個子男人,他叫羅伯特・詹森——頭上戴著一頂白色的頭盔,額頭處用記號筆潦草地寫著他的名字: “ BOB ” 。他們花了兩天時間披荊斬棘才到達失事地點。六天後,詹森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工作人員。
這是里約廷托礦業集團租的一架直升機,原本載著十幾名礦工從秘魯的一座銅礦飛往到齊克拉約市。直升機失事時,里約廷托聯繫的正是詹森。在得知機上人員中有十人喪生後,詹森設計出一套抵達失事地點的方案。在這支由他組建的團隊裡,有兩位秘魯警官、兩位調查員、幾位法醫人類學家以及幾位公園管理員。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清楚,這並不是一次搜救任務。
一般公司只有在遇到極端糟糕的情況時才會聯繫詹森。這種 “ 糟糕 ” 包括一切可怕混亂的事件——飛機失事、恐怖襲擊或自然災害。在打撈屍體、鑒別私人物品或聯繫遇難者家屬這些事情上,詹森並沒有特別的天賦,他有的僅僅是經驗而已。在這個幾乎脫離於現實生活的崗位上,詹森一幹就是數十年,早就名聲在外了。
詹森是凱尼恩國際緊急救援服務公司的老闆,每年處理 6 ~ 20 起國際救援服務業務( 2016 年一年就接手了九起)。這份工作讓他出現在幾乎所有大型事故的頭條新聞中。俄克拉荷馬市爆炸案中,他處理了遇難者的遺體問題; 911 事件發生後,他被傳喚至五角大樓;在卡崔娜颶風後,他還參與了遺體收編等工作。
2008 年秘魯發生的直升機失事事件並不是什麼國際新聞,但搜救任務的複雜程度卻讓詹森畢生難忘。由於氣溫很高,所有東西都是黏糊糊的,無處不在的叢林危險也增加了這次任務的難度。詹森決定讓隊員兩兩分隊,以防隨時可能出現的美洲獅和毒蛇。在出發前,他做了風險評估,發現飛機失事區域有 23 種不同的毒蛇。但他只隨身攜帶了三種抗蛇毒素,所以他要求隊員一旦被咬,一定要在昏迷之前記住攻擊他們的蛇長什麼樣子。
他們的任務是收集所有發現的物品——個人物品、屍骨殘骸以及所有能幫助遇難者家屬了解遇難者最後一刻的物品。但在做這件事之前,他們首先要抵達失事地點。但這根本難不倒工作效率奇高的詹森。
在常人看來,除了黑盒子,飛機殘骸裡基本就是一些沒什麼價值的東西,但詹森依舊仔細地搜尋著一切可能有用的物品。最終,詹森和他的隊友在山坡上發現 110 件骨骼碎片,外加一些私人物品和一個駕駛艙話音記錄器。每個夜晚,隊員都會將他們找到的東西埋起來,然後全體站立為死者默哀。這些遺體和遺物在隔天會被重新挖出來,用直升機運走,隊員隨即開始新一天的搜尋工作。
在山坡上連續幾天地毯式的搜尋後,他們收獲頗豐。然後詹森看到了一樣東西——那是一塊人體組織,高高地掛在陡峭斜坡的一條樹枝上。即便有繩索保護,到那麽陡峭的山坡上把它取下來也相當危險,但詹森無法置之不理。冒著極大的風險,他爬上斜坡取到了那塊人體組織,並將它小心翼翼地放進塑膠袋。搜救隊找到的所有物品都將原數歸還給遇難者家屬。
“ 這樣他們就能知道,至親的遺體不會就這樣被丟在荒郊野嶺裡沒人管, ” 詹森回憶道, “ 即便是殘骸也不能放過。 ” 因為詹森明白,對於遇難者家屬而言,再小的一塊碎片都能帶來莫大的安慰。
一口用於練習的棺材
詹森一行人找到的物品都被運送到了凱尼恩位於布拉克內爾的倉庫內。布拉克內爾距離倫敦有一小時的車程。從正面看,凱尼恩所在的樓和旁邊的樓群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混凝土磚塊砌成的房屋。但穿過辦公室,你會看到一棟像飛機棚一樣巨大的倉庫,所有搜尋回的私人物品都會在這間倉庫中進行拍照、辨別並儲存。

▲訓練用棺材
在倉庫四周的鐵架子上,整齊碼放著凱尼恩公司在無數任務中所用的工具。儲物櫃裡放著隨時都可能用到的衣服和零碎物件,每一套都密封在塑膠袋內。除此外,還有事故專用的急救包以及奔赴衝突地區所需的防彈衣,一箱為穆斯林家庭準備的祈禱毯和一箱為小孩準備的泰迪熊毛絨玩具。一輛冷藏掛車就停在倉庫的角落裡,門半開著,相當於一間可行動的停屍間。房子裡還有一口棺材,緊靠在一堵墻上,上面蓋著紫色的天鵝絨。詹森解釋說,這口棺材僅供隊員訓練使用,不過看起來仍舊陰森恐怖。
一位學生坐在桌子前獨自工作,他正在把這些個人物品的照片處理到白色背景上,以便遇難家屬識別。儘管頂棚被大雨弄得嘩嘩作響,但這間屋子依然安靜得讓人覺得毛骨悚然。
在技術日益高級和精密的今天,大規模死亡事故發生的規模更大;航空旅行變得快捷的同時,飛機失事也顯得更加致命。所以一旦出現事故,人們對專業人士的需求也更加緊迫,這正是凱尼恩走向全球的原因。
如今,大多數人認為給大規模災難收拾殘局都是政府的工作。儘管政府確實會處理一部分——詹森在 1998 年加入凱尼恩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政府軍隊中處理喪葬事務。但在政府處理的事務之外,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像凱尼恩這樣的公司去處理,一各方面是因為它們更加專業,另一各方面是因為它們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2004 年,印度洋大地震引起的海嘯造成超過四十多個國家的遊客在泰國喪生,所有國家都在忙於將遇難者屍體歸還給遇難家屬。但海嘯過後的屍體(的身份和國籍)不易辨別。 “ 這個時候就得靠所有人齊心協力。 ” 凱尼恩不但提供設備支援,作為公正的調解人,在國籍和種族上也絕不會厚此薄彼。

不管是從哪個方位看,凱尼恩前排的辦公室和其他公司的辦公室都沒什麼差別,但凱尼恩卻精心布置各個辦公室的方位,以備應對大規模傷亡事件。
除了應對恐怖襲擊事故,詹森大多數的工作都與航空事故有關。大多數旅客認為,飛機失事後,航空公司理應承擔隨之而來的眾多責任。但航空公司和政府往往會聘用類似凱尼恩的專業公司,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多餘的人力和精力去應付這項複雜且浩大的 “ 工程 ” 。因為航空公司除了要安慰遇難者家屬,還要想辦法應付賠償金。
連續幾年的訴訟和負面新聞對航空公司更是致命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仍在 MH370 和 MH17 的餘波中艱難掙扎(詹森提醒我好幾次,馬航並不是凱尼恩的客戶)。這個時候航空公司就可以把一切事務交由凱尼恩處理;的服務包括組織客服中心、遇難者遺體確認和遣返、集體埋葬、私人處理等等。
航空事故的善後工作被如此重視也就是近 20 年的事情。 1994 年,全美航空 427 號班機在匹茲堡附近墜毀後,遇難者的私人物品居然在垃圾桶中被人發現,這引發了家屬大規模的不滿和抗議。一位家屬在給航空公司的抗議信中寫到: “ 誰能決定哪些私人物品是重要的,哪些又應該被掃入垃圾箱?我們現在談論的是人啊!在某些情況下,就算是一個行李標籤,也能給家屬留個想念。 ”
但即便到了今天,一些國家在相應的法令法規建設上依然滯後。前美國交通部監察長兼航空律師瑪麗・夏沃告訴我,有一次,委內瑞拉發生空難後,當局在搜尋遇難者遺體一事上敷衍馬虎,用當地農場借來的裝載機像推土一樣清理遺體。 “ 這些年我碰到了太多處理遇難者遺體的國家機構或者私人公司,他們沒一個像凱尼恩一樣專業,尤其是在細節上差別真的很大。 ”

▲凱尼恩的辦公室大廳內擺成一排的飛機模型,是航空公司客戶送給詹森的禮物
“ 哪有什麼所謂的釋懷啊! ”
詹森通常會用最少的時間掌握事故的全部相關資訊,確定航空公司最急迫的需求。根據事故的嚴重程度,凱尼恩能迅速召集到多至 900 位專業救援人員。凱尼恩的隊員並非來自單一產業——儘管很多人都曾在執法部門供職——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同情心。詹森時常提醒他們, “ 不要帶入個人感情。 ” 詹森有一個習慣,他絕對不會和遇難者家屬有過多聯繫,因為這樣會讓他覺得自己是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
詹森處理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項便是協調停屍間。遇難人數並非和需要的停屍空間成正比。 2013 年,一架小型飛機在莫桑比克墜毀,但它在租用停屍間上的花費卻比一些大型商業飛機還要多——儘管這場墜機事故中只有 33 名乘客死亡,但卻回收了 900 多片人體殘骸。
一有新消息詹森就會立刻向家屬通報。這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詹森嚴肅地說道: “ 發生的事情無法改變,你能做的就是不要讓它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 他很想給家屬帶來一絲希望,但情況總是恰恰相反,他能給家屬的往往都是冰冷殘酷的現實。 “ 你們要明白的是,飛機撞擊的速度非常快,這也就意味著你們的至親已經毀了模樣,這也意味著我們可能會找到幾千塊人體殘骸。 ”
詹森不喜歡用 “ 釋懷 ” 二字。 “ 我從來沒見哪個家庭 ‘ 釋懷 ’ 過, ” 他說, “ 他們經歷的只不過是一種常態到另一種新常態的過渡。 ” 失去至親後的過渡往往都很艱難,但飛機失事後的眾多不確定性讓這種過渡更加難以完成。遇難者家屬通常一連幾週都見不到遺體甚至是殘骸。見不到遺體也就意味著無法最終確認,也無法申領保險,更不用提什麼 “ 入土為安 ” 了。所有家屬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進一步的消息。
當遺骸和個人財物陸續抵達倉庫時,凱尼恩的員工會小心翼翼地打開每個箱子,將物品放在房子中央的網狀長桌上。經過檢查的物品會分成 “ 有關聯 ” 和 “ 無關聯 ” 兩類放置。 “ 有關聯 ” 物品指的是貼著乘客姓名的物品,以及在遺體上或附近發現的物品; “ 無關聯 ” 物品裡是尚未確認擁有者身份的物品,這裡面有從廢墟裡發現的手錶,還有無法辨認乘客名字的行李等。 “ 有關聯 ” 物品會先歸還給遇難者家屬, “ 無關聯 ” 物品則會被拍攝下來,傳到網路上,供家屬進一步識別。
儘管很簡單,詹森卻從未放棄努力將那些 “ 無關聯 ” 物品與遇難者相匹配。他們會利用任何可用線索,包括從相機內恢復的照片以及手機中調取的手機號碼。詹森甚至把車鑰匙帶給了汽車經銷商,看看他們是否能夠提供車輛識別號碼。經銷商通常只能告訴他這是哪國出售的車,但這對詹森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資訊。比如,有一次,詹森在德國之翼航班失事現場發現了一串車鑰匙,在他得知車是在西班牙出售的資訊後,大大縮小了匹配遇難者的範圍。
識別私人物品要比識別遺體痛苦得多。 “ 你在做屍骸鑒定的時候,只需要做身體檢查就可以了, ” 詹森解釋道, “ 和家屬聊聊,透過談話來收集資訊,你只需要這些資訊來確定身份。但當你識別私人物品時,你得全各方面了解這些人。他們的播放列表裡有什麼歌?你不是真的要關注他的播放列表都有什麼歌,而是要對比他們的電腦上的列表,看看能不能確認這是誰。 ” 私人物品也是有感情的。當你看到遇難者前幾週剛拍的結婚照時,你無法做到不同情遇難者。
物品歸還的每一個步驟都必須和遇難者家屬進行溝通。詹森和我們分享了他的一次經歷,他曾遇到過一個在 1988 年洛克比空難中喪失女兒的母親,當她收到女兒的遺物時,她對這些物品散發的燃料氣味感到惡心——整個屋子都是這種氣味,久久不能散去——不過,過了一段時間,她就開始接受了這種氣味,因為這能讓她想起她的女兒。
“ 同時,你也不能替家屬做決定,你會遇到這樣的母親,她也許會說, ‘ 我給兒子洗了 15 年的衣服,最後一次替他洗襯衫的人怎麽能是你們,必須得是我! ’ ”
一只腳穿著高跟鞋的女人
對於那些不想前來(或者沒準備好來)認領私人物品的家屬,詹森會將這些物品存起來,有時一存就是兩年。有時候,這個時間可能會更長。成箱成箱的 “ 無關聯 ” 物品摞成幾排,高高地佇立在倉庫一側,空氣裡隱隱約約飄著一股飛機燃油的味道。
儘管這些遺落之物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但我能感受到它們的死一般的沉重氣息。詹森從一個箱子裡拿出一個塑膠袋,袋子裡是一本護照,角上的圓孔是為了預防身份盜用才打穿的(遇難者名單通常會在飛機失事後公布,身份盜用和欺騙性索賠屢屢發生)。
很多詹森找回的東西都沒有歸還家屬。兩年後,或者是更長,直到沒有調查立案,最後這些東西會被銷毀。但詹森卻無法像銷毀遺物一樣抹去那些隱在背後的故事。比如,他想起了一個在俄克拉荷馬市爆炸中喪生的女人,一只腳上穿著高跟鞋,另一只上穿著平底鞋。他意識到,這個女人肯定是剛到辦公室,爆炸發生時她正在換鞋子。如果那天她遲到五分鐘的話,或許她還活著。
那詹森有沒有設想過自己真遇到了這種事情時會怎麽處理呢? “ 還是希望逝者能給生者留點兒想念吧。要真發生這種事,我反正希望能給布蘭登留下點什麼。 ” 他邊說邊向他的愛人布蘭登・瓊斯點頭示意,布蘭登是凱尼恩的營運長。 “ 婚戒、手鏈什麼的都行 ” 詹森和瓊斯都戴著彼此送的編織手鏈, “ 就是那些特殊意義的東西。不過他可能想把這些東西賣掉吧。 ” 他打趣道。
瓊斯想了一會, “ 有點奇怪, ” 他說, “ 我沒有飛行焦慮。在我加入凱尼恩之後,我對生命的看法也沒改變。不過,在某些東西的重要性上,我的看法確實發生了變化。我隨身攜帶的東西一直都在我的包裡,一直都在。他去其他地方給我帶的紀念品,我也經常帶著。這些東西雖然不會一擡頭就能看到,但在我把護照放進包裡的時候,我就能看到它們。我知道這些東西對他來說是有意義的,我覺得帶它們上飛機,如果失事後他能收到做個紀念,他也會安心繼續前行。 ”
儘管這份工作讓詹森明白擔心災難發生根本沒用,不過他依舊在入住飯店時數清自己的房間離逃生出口有多遠;登機後,他和瓊斯等待安全帶標誌燈熄滅後才脫下鞋子(大多數飛機失事均發生於起飛和降落期間,你絕對不希望光著腳在柏油碎石跑道上逃生)。我之前還在猜想,在恐怖主義肆虐的時代,詹森是如何做到鎮定地活著的,他是不是有什麼秘密沒有說出口,後來我才明白,原來他的秘密就是:縱容你對現實的焦慮,不要把時間浪費在恐懼上。
一盒橘黃色的捲髮夾
大多數家屬傾向於透過郵寄的方式收領遺物。但一些家屬希望親手遞交,這才是最難的部分。有一次,詹森受命將一位年輕小夥的私人物品歸還給其家屬。在飛機失事前的早些時候,他給他的媽媽打了一通電話,告知她自己要登機了。當她打開電視看到他所在的飛機跌入大海時,她知道自己的兒子出事了。
詹森很清楚地記得這件事。這位母親不確定自己的兒子是否已經身亡。有沒有可能遊到了附近的島嶼上了呢?海岸警衛隊可以前去查看一下嗎?他們的確去查看了。飛機失事的幾天後,幾乎所有遇難乘客身份得到確認,但收回的人體組織沒有一塊屬於她的兒子。
隨著乘客的物品被海浪沖上海岸,他們發現了她兒子的物品,包括兩本浸透水的護照,還有一個行李箱。凱尼恩打電話通知她,向她詢問是透過郵寄還是親手遞交。她選擇了後者,詹森主動請纓前去遞交。
詹森還記得自己抵達她家時的情形:她兒子的卡車靜靜地停在車道上;他的房間和離開前一模一樣,絲毫沒有動過;她辭掉了工作,了無生趣地生活著,就像死了一樣。 “ 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 詹森回憶道, “ 因為沒有證據,沒有屍體。 ” 詹森和他的同事清理出一張桌子,鋪了一張白布。他們要求這位母親先離開這間屋子,緊接著開始把她兒子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擺放在白布上。他們把這些物品蓋了起來,這樣她走進屋子的時候就不會因為看到這麽多物品而被悲痛全然吞噬。擺放完畢後,詹森叫她進來。
有一件物品一直讓詹森感到疑惑。在收回的行李箱裡,他們發現了一盒橘黃色的捲髮夾,和詹森的母親在 70 年代時用過的一樣。但這個年輕人是短髮,這似乎不太合理。詹森猜想,估計是漁夫發現行李箱半開著,就把其他乘客的東西放了進去。 “ 請不要生氣, ” 詹森將捲髮夾展示給她的時候說道。
她確認這個捲髮夾的確是她兒子的。他借的是他外祖母的行李箱,她習慣把它們放在行李箱裡。他知道這些東西對外祖母非常重要,所以就把它們放在了隨行的行李箱裡。詹森一直忘不掉那位母親當時看他的眼神, “ 羅伯特,你是在跟我說,我的孩子再也回不來了,是嗎? ”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