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卡爾•伊坎 (Carl Icahn) 。大家都知道伊坎,不需要我介紹了。我們會議的主題是長期投資。有人說卡爾•伊坎的投資風格是短期的,雖然伊坎認為自己是長期投資。我們聽聽伊坎怎麼說。
歡迎卡爾•伊坎。卡爾,歡迎!我們今天一整天討論了長期投資、短期投資、回購、股息,積極投資者給公司施加的壓力、對公司的影響。我們想聽你講一講,你是支持長期投資還是短期投資?
伊坎:積極投資者各有各的風格。積極投資者也分許多種。你們邀請我的時候和我說了“別人都說你的風格是短期投資,但是你手裡的很多股票都持有很多年了,一定要來這裡給大家講講”。
我一般不這麼做,這次我列了一個表。大家肯定不願意聽我讀東西,我就很快地讀一遍。
大家看看我們買的公司,連我自己都很吃驚,這些公司我們竟然投資了這麼長時間。ACF,我持有了 31 年,連我自己都不敢承認,31 年。美國軌道車輛工業公司 (American Railcar Industries),23 年;PSC 金屬 (PSC Metals),17 年;輝門公司 (Federal Mogul),14 年;威蓋世 (Viskase),14 年;XO 通信 (XO Communications),14 年;美國賭場與娛樂集團 (American Casino),11 年;美國能源集團 (National Energy),11 年;西點家紡 (Westpoint)、11 年,等等。
我們和許多積極投資者一樣,都不是只看短期的,雖然不是所有積極投資者都這樣。有的是,有的不是。有合夥人的時候,合夥人都要收益,不看短期也不行。我這麼多年,真正賺大錢的投資,是持有 7 年、8 年、9 年的公司。回頭看我們買的那些公司,一定要在根本沒人要的時候買,這就是最大的秘密。
聽起來多簡單,做起來就很難了。所有人都討厭的時候,你就買;所有人都想要的時候,再賣給他們。我們就這麼投資的。
我們把公司收了,然後把公司清理乾淨。經營好的公司很多,但是經營特別爛的公司也很多。公司裡沒民主可言,現在還是沒有。這些經營公司的人,他們也不是壞人,但他們經營公司不稱職,就沒這個能力,或者只想著自己的私利。
我舉個例子說一下美國公司是什麼樣的。你叔叔給你留下了一個葡萄園,特別漂亮,有果樹、有鮮花,美極了。你走運了,又能享受葡萄園的美景,又有大筆錢可賺。八個月後,你朋友來看你。
你朋友問:“最近怎麼樣?”
你說:“不怎麼樣,一點也不好。”
朋友問:“怎麼了?”
你說:“葡萄園很好,很漂亮,但是管理員吧,整體打高爾夫,還自己租了架飛機,給女朋友開宴會。什麼活都不做,還經常把葡萄園的東西拿出去賣。一分錢都不給我。”
朋友說:“你傻啊?叫警察來,把他踢出去。”
美國公司就是這樣,很多美國公司都這樣。美國公司的管理層就這麼做的,他們把自己當成了公司的主人,為所欲為。我這麼多年能賺這麼多錢,就是因為我讓這些人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些管理層和董事會關係很好。董事會裡的人都是朋友,董事們和 CEO 也是朋友。不過,我們進入公司一兩年後,很多董事聽我們的。我們能賺這麼多錢,不是因為我們會選厲害的股票。我覺得沒有能總選中厲害股票的人。我們進入公司,把公司的問題清理掉。有時候我們也搞不定,搞不定就要等很多年。
這是我們國家的問題,許多公司經營有問題,我們很快就會付出代價。我不是說美國公司都沒有好管理層,出色的管理層和董事會也很多。至於未來,從現在的情況看,我同意 Stanley 說的,問題很大。現在聯準會實施這樣的政策,我們將來可能走到地雷區裡。這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問題很大。
主持人:我們可以稍後再聊聯準會。再回到積極投資者的話題,你剛才說了你長期投資的一些公司,就看這些公司,你覺得就這些公司而言,你做的投資是積極投資者做的嗎?還是就是普通的投資?我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現在你看上了 AIG。我們可以聊聊 AIG。你希望把 AIG 拆分。我覺得你只是想買入 AIG,把它拆分,然後就退出,對嗎?
伊坎:不一定,有的時候是這樣。既然你提到了我剛才說的那些公司,我們就看其中的第一個,我現在還持有呢,ACF,31 年了。我講一個關於 ACF 的小故事。請大家耐心聽我講,是個很短的小故事。
那是 31 年前,我那時候還很年輕。我是個工作狂,總是在看公司、投資公司,我發現了 ACF,這家公司的股價是 30 美元。我研究這家公司生產的列車,研究它的所有資產。這家公司根本不賺錢。我是老派,相信葛拉漢 (Benjamin Graham) 和陶德 (David L. Dodd) 的理念,現在也沒變。一看這家公司,太便宜了。我把當時所有的錢都投進去了,雖然沒法和現在比,我當時錢也不少了,大概投了 4、5 億,有些錢是借來的。我買了很多這家公司的股票。
我們買入這家公司後,更是發現太便宜了,這麼多資產,才 30 美元,雖然它一分錢不賺,管它呢。後來,我取得了這家公司的控股權,這家公司是我的了。控股以後,我開始深入瞭解。我數學很好。我不會親自插手企業的日常管理工作。於是,我和 CEO 見了一面,他說:“伊坎先生,歡迎你。我們之間有過一些爭執,但是現在你進入了董事會,我們還是歡迎你的。”我說:“好啊,我們現在是朋友了。”
這家公司生產軌道車輛,具體我就不多說了,公司下面有很多子公司。軌道車輛公司的秘密也很簡單。公司生產軌道車輛,政府想刺激生產。政府規定軌道車輛的折舊年限是 5 年、6 年、7 年,但是軌道車輛可以用 40 年。折舊這麼高,能帶來極大的稅收優惠,公司賺錢的秘訣就在這裡,可以利用稅收優惠。可是公司裡的這幫人一直在收購其他公司,買的每家公司都虧錢,這就是這家公司的問題。
我去了這家公司,它在紐約第三大道有一棟 12 層的辦公樓,是黃金地段。我說:“這家公司是你們管的,活都是你們做的。”我講的是真事,雖然當笑話講的,但是今天很多公司就是這個情況。
我往下講,你們可能都不信。於是,我就開始瞭解公司的情況。我數學很好,對數字很敏感,撲克打得也不錯。我要弄清楚這家公司是怎麼經營的。他們和我說:“伊坎先生,我們去 12 樓吧。”我們就去 12 樓了。
我拿了一個黃色的記事本,他們就給我講,這人負責這個,那人負責那個,這個人在 7 層,那個人在 8 層。我足足花了一天時間,晚上回到家,把黃色的記事本拿出來,怎麼看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經營的。
第二天,我又回去了,7 樓、8 樓、9 樓,到處跑。我不是笨蛋,可我弄不清他們在這公司裡都做什麼。他們說,這個人是做這個的。我問:“為什麼這個人要做這個。”他們說:“這東西太複雜了,你搞不清楚的。”好吧,最後我說:“我想見 COO。我要見負責第一線管理的 COO。”他們說:“別去了,伊坎先生,別去了。”我問為什麼不去?他們說:“他們都怕你。”我問:“怕什麼啊,我怎麼把他們嚇成這樣?”這些人說:“他們要靠我們,我們給他們發號施令,他們怕你和我們。”
我說我不會嚇唬他們,我就想見見 COO。見一面會怎麼樣?我又從 8 樓到 7 樓,最後回到家,還是搞不清這家公司到底怎麼回事。我罵了髒話,我給 COO 打了電話,他叫 Joe,在聖路易斯辦公。我說:“Joe,我想去和你見一面。”他說:“沒問題,伊坎先生,歡迎你。”我和他說:“幫我個忙,別告訴 CEO 我去見你了。我就想一個人去,和你聊聊。別緊張。”他說:“我為什麼要緊張啊?”我說:“對。”
這個 Joe 是個像 John Wayne 一樣的硬漢,曾經在海軍陸戰隊擔任上尉,我倒有些怕他。我們聊得很投機,有說有笑。他給我講他的工作,我能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我說:“我請你喝一杯。”我們就去喝酒了,喝著馬丁尼的時候,我說:“Joe,我問你個事,你別多心,我沒藏著什麼,你別緊張。”他說:“我為什麼要緊張啊。”我說:“你在這邊負責公司的營運,紐約那邊有一幫人,你告訴我,你需要紐約那邊有多少人支持你的工作?因為我搞不清他們一整天都在做什麼。
他說:“我告訴你,你該做什麼。我告訴你,我需要多少支持。我需要減少 30 人。”我說:“減少 30 人是什麼意思?”他回答:“這樣就沒那些老闆了,我告訴你怎麼做就行。”我說:“這樣就行?具體怎麼辦?”Joe 說:“明天就把他們全開除了,一個不留。沒了這 30 個人,我就不用支持他們,給他們提供數據了,他們要這些數據也沒用。”
我說:“怎麼可能呢?我不信。”要是放在現在,我肯定馬上就辦了,把這 12 層樓的人全趕走,當時我還還懷疑這個 Joe 可能不太正常,我怎麼能把整整 12 層樓的人都開除了呢?
我就琢磨該怎麼辦。我認識這幢辦公樓的所有人,他和我說:“卡爾,你要是搬出去,我可以把樓租給別人。這幫人天天什麼都不做,我都看著呢。”我心裡想說“這傢伙是個搞房地產的,懂什麼。”
我知道該怎麼辦了。正好手邊有一個顧問。顧問雖然經常沒什麼用,有時候還能幫上些忙。我把這人叫來,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還不錯,是個專家。他們來了三個人。教授對我說:“伊坎先生,我們瞭解你的問題,非常複雜。”我說:“是啊,他們也這麼說,非常複雜。我想知道他們都做什麼的。”教授說:“別急,給我們三週的時間,費用是 25 萬美元。”我說:“行,給你 25 萬美元,三週後來告訴我。”
三週後,他們來了。說起來你都不信,三週後,他們回來了,拿著一大疊資料,還有各種圖表,黃色的、綠色的、紅色的。我說:“這些東西我可看不了,再說我還是色盲。我要的很簡單,這有個記事本,我上學的時候成績很好,我對數字很敏感,你就告訴我他們都做什麼的。”我接著說:“給你,這是你的 25 萬美元。”他笑了,對我說:“伊坎先生,你不拐彎抹角,你是個好人。我也和你實話實說,我們也不知道他們都在做什麼。”
我不是講笑話,這是真事,就這麼好笑。我說:“去他媽的。”我直接給 Joe 打了電話。他說:“太好了,就這麼辦。”我給那幫人發了補償金,他們都沒脾氣。12 層樓的人,都給開除了。我花了 1000 多萬,當時不是小數目。就算是個雜貨店,你買下來,然後給關了,也會有人抱怨幾句。可是我把這 12 層樓的人都給開除了,沒一個人找我。就像科幻電影裡演的一樣,他們好像從沒存在過。沒一個人給我寫信,沒一個人給我打電話。就像我扔了個炸彈,樓還在,這些人都被炸死了。這是我的原則,我做很多事情都這樣。很多公司,其實誰都沒錯,就是 CEO 太不負責,還拿著很高的薪水。今天的情況很危險,大量平庸的公司在借錢,它們借錢的成本非常低。
主持人:有一種觀點是一些 CEO 把借來的錢用於回購、分紅,因為他們害怕你,是在防你。
伊坎:我知道他們都這麼說,其實不是這樣。他們回購,是因為他們有期權。他們想讓股價上漲,這才是他們關心的。人性如此。他們很清楚他們不勝任自己的工作。他們心知肚明。他們不但不勝任,而且根本不想工作。這些傢伙都是高爾夫球高手。就算被我盯上了,他們也會說“沒事,我們繼續回購”。
我們的很多公司本益比都快 30 倍了,因為它們一直在回購,通過回購提升盈利。每個公司情況都不一樣,但很多都是在回購股票、低息借款,然後回購股票、虛增盈利,盈利絶對有高估。
很多公司都在折舊上動手腳, Valeant 就是個典型例子。做這種手腳的公司很多,但 Valeant 比較過分。分析師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公司對分析師說 GAAP 利潤不重要,分析師也說不重要。
Valeant 收購其他公司,因為其他公司有好的產品,但是他們不攤銷商譽,他們說還會接著收購其他公司,以後業績會更好。分析師就買帳了。公司的盈利裡面灌水太大了。 Valeant 收購了很多公司,都是無形資產、商譽,提供業績指引的時候,也不攤銷。
主持人:你看到我們昨天採訪 Bill Ackman 了嗎?
伊坎:沒看。我知道他會說什麼。我和 Ackman 不是敵人了,我們不打了。我們現在是朋友。好朋友有時候也爭吵。關於康寶萊 (Herbalife),我們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主持人:你沒買 Valeant 吧?
伊坎:沒。我不想說我完全沒買。我不告訴你我買還是沒買,這不重要。我就是舉個例子,想到了 Valeant ,就用了 Valeant 。關鍵是很多公司都這麼亂來。美國的很多公司往利潤裡灌水。看一眼就知道了。我可是靠這吃飯的,很多公司虛增利潤,我很清楚。將來會有一天,也許是將來的一個星期,會吃到苦果的。具體是什麼時候就不知道了。這個問題很嚴重。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個新聞。
主持人:什麼新聞?
伊坎:聯博資產管理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說,ETF 基金非常不安全。確實不安全。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說到衍生品時說,衍生品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ETF 基金也差不多。拉里•芬克 (Larry Fink) 是個好人,我們是朋友。如果他沒覺得不安全,他又為什麼要保證流動性?等所有人都想賣出 ETF 的時候,誰來接盤?拉里•芬克嗎?這是我的觀點。
主持人:比爾•阿克曼和拉里•芬克都是你的好朋友?
伊坎:我沒說拉里•芬克是壞人。芬克做了自己的分內事,他幹得很出色,推銷做得很好。這是他的工作,他就該這麼做。他的工作是給貝萊德(BlackRock, BLK-US) 賺錢,他做得漂亮。我認為,不只是 ETF,整個體系都走到了懸崖邊上。
主持人:一會我們再接著聊這個,暫時再回到積極投資者的話題。說說比爾•阿克曼吧。積極投資者有做對的時候,也有做錯的時候。我提到比爾,是因為他取得過轟動一時的成功,但是在康寶萊上就沒成功。在 JCPenny 上更是栽了大跟頭。你擔心自己做出錯誤決策嗎?
伊坎:誰都會犯錯。這麼多年,我學到了一個經驗,要保守一些,要手裡有資金……說實話,我就是因為這個才不做對沖基金了。
我管理過對沖基金。我是很照顧合夥人的。當所有人都想把資金撤出去的時候,我可以不給他們,因為約定的投資年限是三年,但是我沒這麼做。我和這些人達成了協議,我把自己的錢拿出來,讓他們退出。這是我收益最高的一筆投資。我拿出了 15 億左右。就在所有人都想把資金撤出來的時候,我把資金還給他們了。
關鍵是管理對沖基金和做積極投資,這兩件事就是有衝突。我覺得很難合到一起去。我交了很多朋友,也賺了很多錢。如果資金不是沒期限的,或者期限較長的,很容易就會被逼到死角裡。
週期總是存在的。例如,我們在 Chesapeake Energy 上還在虧錢,在 Transocean 上還在虧錢,我們的整個能源投資還不錯,是因為 CVR Energy 先好轉了。我是這麼想的,可能我的想法很奇怪,可能完全不符合常理。
我說了,你可能不信。這些公司,我根本不在乎它們跌。因為我自己知道,下跌了,我會買更多。這些公司,我現在就等著買入更多。
你可能覺得不合常理,但我一輩子都這麼做的。這些公司下跌的時候,我手裡有錢,有彈藥接著買。到時候你們可能會笑我,說萬一出現經濟危機怎麼辦。可是,2008 年,2009 年,在很多公司上,我都是買入的主力。
主持人:前面說到了 AIG。AIG 現在上了新聞。你確實想把 AIG 拆分。你是要星期四去見 AIG 的 CEO 嗎?
伊坎:他來見我。
主持人:他來見你,不是你去見他。你們會說什麼?能不能告訴我們?
伊坎:我們很友好。這次,我只請他去我的辦公室。過去,我們買 Family Dollar (折扣零售商) 的時候,CEO 是從田納西州來的,我們一起在我家吃飯。我知道他是個好人,我們有說有笑。我遞給他一杯馬丁尼。他說:“謝謝,但是一會我們要開會,我得保持清醒。”我說:“你不喝也沒用。” (笑)
Q & A
提問:你認為其他機構投資者會支持你嗎?你上週寫了一封關於 AIG 的公開信。我想問一下,其他機構、資產管理人,是否會支持你關於 AIG 的計劃?
伊坎:我之所以公開說,是因為我覺得 AIG 顯然就該拆分。在這種十分明顯的情況中,大家知道,這麼多年,我已經因為這個出名了,幫基金賺了不少錢,所以它們就會聽我的,確實聽我的。
另一方面,我想聽聽 AIG 的看法。AIG 的 CEO 漢考克給我打電話說要見我。我會聽一下他怎麼說。我真不知道,他為什麼說不能拆分。我覺得毫無道理,但是我也不想批評他。對待這些事情,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他可能有他的想法要告訴我,他的話可能會讓我改變主意。
提問:今年 5 月份,你投資了 Lyft 公司,你投了 1 億美元。之前,在此次會議上發言的人說 Uber 很了不起,只有 Uber 一家能活下來。你認為其實兩家都能活下來。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主持人:你投資了 Lyft。Uber 的早期風險投資人克里斯•薩卡 (Chris Sacca) 今天上午也在這。你認為這兩家公司能否共存,就像 AT&T 和 Verizon 一樣?或者還是這是一個贏家通吃的行業,只有 Uber 是最後的贏家。
伊坎:這還用說,要是我覺得只能剩一個,我也不會拿 1 億美元投 Lyft。我覺得答案很明顯。我做套利很多年了。Uber 值 550 億,Lyft 才值 20 億,也太低了。要是在過去,我會做空 Uber,做多 Lyft。因為沒辦法做空 Uber,我就買了 Lyft。我覺得 Lyft 有很大的機會。
提問:我的問題是關於做空倉位的披露。紐約交易所提議,SEC 應該要求對沖基金不但要披露做多的倉位,還要披露做空的倉位。你怎麼看?是否應該披露?
伊坎:這個我沒考慮過。我得看到具體是什麼內容,才能評價,但是我真沒想過這個問題。
提問:伊坎先生,你提到了 Valeant 公司。人們批評 Valeant 不道德,它看好了其他公司的產品,就把這家公司收購,然後遣散所有員工,以此抬高自己的股價,還把相關藥品的價格漲到原來的 50 倍。你投資這樣的公司時,會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嗎?你會投資不道德的公司嗎?
伊坎:我是個老派,過去我們講究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話聽起來老掉牙了,現在人們不講這個了。
說到 Valeant ,我想說清楚,我提到它,不是為了專門批評它。我只是用它作一個例子。我想說明的是,今天的許多公司,我們看一下它們的盈利就會發現,它們連無形資產都不攤銷。
很多資產沒攤銷,盈利灌水太大。我花時間研究了,我覺得標普指數就要達到 23 倍本益比了,這可不是 17 倍,太高了,何況現在還是零利率。我不是說市場明天就會跌,我也不會明天或下周或下個月甚至明年就做空,但這確實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利率這麼低,公司的盈利都是虛的。我不是批評 Valeant ,而是批評這種虛增盈利的做法。
提問:你好。今天上午拉里•芬克也出席了。他說,他非常積極地參與他們投資的公司,只不過沒公開他們做了什麼。我想問一下,他們與積極投資者的做法有什麼不同?為什麼與積極投資者相比,由資產管理人推動的改變這麼少?是因為與公司打交道的方法不同,還是分析師與私募股權投資者的角度不同?或者是因為存在長期策略與短期策略的區別?
伊坎:我說了,芬克是個好人。但是從很多方面來說,他都不算是積極投資者。我知道,他自己肯定不同意我這麼說。我覺得指數基金沒出多少力。他的工作是給指數基金吸引投資者。利益出發點有些不同。他們打交道的是那些公司,公司投資買他們的基金。既然公司投錢買他們的基金,他們怎麼能和公司做對?他們又怎麼會成為公司的威脅?他們說他們確實做研究、確實解決問題,我敢說他們肯定不會投票支持我。
很多其他基金就不一樣了,它們越來越傾向於採取積極投資的態度。很多基金給我們打電話,讓我們看看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因為這些基金和指數基金的投資不一樣,它們對積極投資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提問:你好,我是紐約城市大學的學生。對於希望進入這個行業,在行業裡取得成就的學生,請問你能給一些建議嗎?
伊坎:你想入行?好吧。
主持人:是好,還是不好?
伊坎:我覺得不是不好。問題是我剛說過了,將來情況會很糟,今後幾年,這行會很難做。我不是對下週或明年表示悲觀,但是公眾將來會為他們現在的行為買單。現在泡沫正在形成,或者已經形成了,高收益債券、垃圾債券,一旦出問題,就是從懸崖摔下去。
政府說得對,政府說了,我們不管大而不倒那一套了。到時誰來接落下的飛刀,沒人接。所以我覺得,今後幾年,公眾會感到美夢破滅的痛苦。我不是說不讓你做這行。我的意思是,你看那些頂尖的投行,他們怎麼賺錢?就是提供諮詢服務、募集資金賺錢。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付錢給他們,我們是儘量不給他們多少錢。
要是你做得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行業。從風險和收益的角度考慮,對你很有利。要是你管理對沖基金,好處就更大了。你根本不承擔風險,除非你自己也投錢。但是如果你真想賺大錢,就要去冒險,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別光靠給別人管錢來賺錢。說實話,你說有哪個人真能知道哪個股票會漲、哪個會跌。這樣的人,我根本沒見過。
我覺得,你要經歷很多年,自己去找公司,像養孩子一樣,你喜歡自己看好的公司,甚至希望它下跌。這就是葛拉漢和陶德教的方法,告訴你怎麼發現便宜的股票。
今天的情況很有意思,我兒子進入這行十年了,他很用功。蘋果(Apple, AAPL-US) 就是他告訴我的,我覺得 Apple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公司。
最奇怪的是,這是一個符合葛拉漢和陶德方法的公司。因為 Apple 的價格就是本益比的 8 倍、9 倍。你就要找到這樣的公司,像養孩子一樣養著,等待,耐心地等待,就能賺錢。可是,今天有些人賺了幾百萬、幾千萬,都是收管理費、吸引客戶賺的。我不想得罪人,因為這些人裡有我的朋友。你聽聽這些人說話,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主持人:謝謝我們今天的嘉賓卡爾•伊坎。感謝各位的提問。感謝在場的所有觀眾。
《雪球》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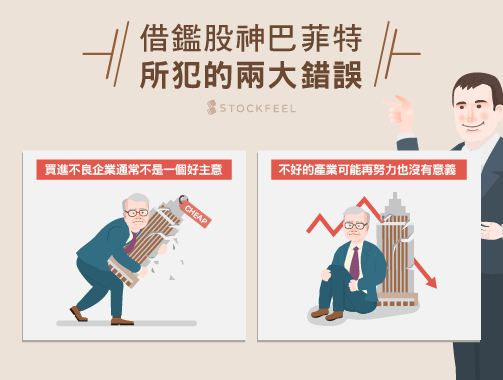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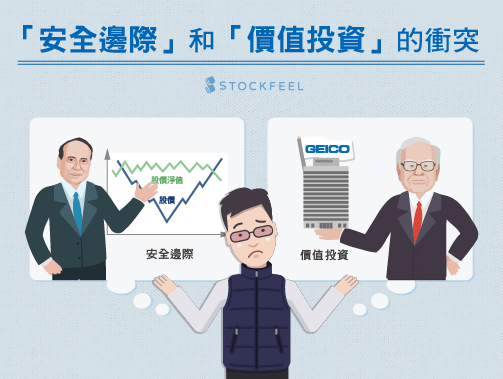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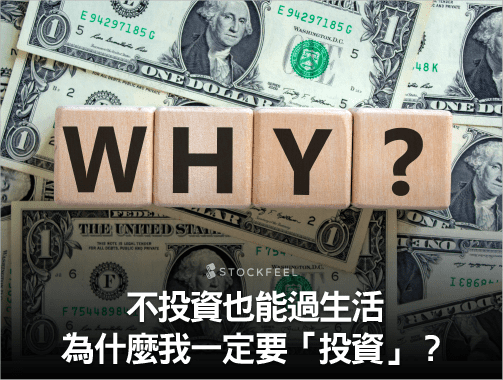

特斯拉與Solar-City間的秘密-華爾街究竟有多醜陋ai.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