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提爾(Peter Thiel)在《從 0 到 1》這本書裡談到非共識的問題,他說:“我在任何有面試機會的場合都會問:在什麼重要問題上,你會與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這個問題是拋給我,那麼我可能會想一想之後回答說:“我認為,中央銀行不能讓這個世界更好。”
“中央銀行讓整個金融體系更為穩定。” 這句話是一個謎,因為好像沒有任何人證明過這個命題。
沒有了央行,或許會少了信貸擴張刺激下的繁榮,但整個系統會不會更不穩定?經濟週期會不會更加大開大合?我是真的很懷疑。各國的中央銀行每天指點江山、運籌帷幄——但所謂面子請人吃一支煙,裡子就得殺一個人;你做了那麼多事,結局就是熵增,永遠不是平穩。
而歷史上已有許多證據,證明若沒有央行的金融世界,也能穩如老狗。
比如四川的交子(中國四川在北宋時期流行的票據和紙幣),就是民間自發的貨幣系統。當時的四川缺銅,蜀人以鐵為通貨,用的錢沉重無比,再加上蜀道崎嶇無比,運錢如同抬棺材,於是運輸的痛苦倒是逼得民間智慧迸發出靈感的小火花,終於用出了交子這個當時的比特幣,以複雜圖案與秘密暗號來防偽。在十世紀後半段,交子完全由私人商販運作,成了百分之百的去中心化。
除了山寨、偽造橫行,私營交子從制度設計上並無漏洞,解決了鐵錢無比沉重的實際問題。然而此制度裡並沒有統一發行交子的央行戲份,體系卻無比穩定。當然有人會說交子不是現代金融,過往的玩法不豐富,自然很穩定。
歷史上還有一個 2.0 的版本,無央行裸奔的另一個實驗,是十八、十九世紀時的蘇格蘭,當時蘇格蘭有三個特許銀行——蘇格蘭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Plc., RBS-UK)、英國商業銀行 British Linen Company,以及十來家無特許的小銀行,交織成一個無比平穩的金融生態。(事實上蘇格蘭大約從 1720~1840 年間都貫徹了這種自由銀行制度)
肯定會有人問自由銀行(Free Banking)是怎麼玩的?很簡單,在蘇格蘭無央行化的自由制度之下,儲戶將黃金存入銀行,所有銀行都能根據黃金儲備發幣,而任何人持幣可以向銀行換回黃金。在每個繁忙的工作日,銀行之間都會像踢開手榴彈一樣,將對方銀行的紙幣透過票據交換所(Clearing House)進行清算,生怕其他銀行的紙幣暴雷。
如此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所有銀行都格外留意自己與其他銀行在外的幣量與黃金儲備之間的比例,這就是你的全部信用與立身之本,大家等於被一根大鐵鍊綁在一起,任何一家銀行若想要超發貨幣、想要擴張信用、想要超借貨幣,就會發現一整天下來要清算的自家鈔票比別家的鈔票來得多,於是只能損耗掉自己的儲備,不然就會違約。
於是,除非所有銀行串通好一起超發貨幣,否則若單獨幾家銀行企圖搶跑,是會被大鐵鍊給絆死的,所以你會發現自由銀行根本就是名不副實、名存實亡、名不配位的存在,一點都不自由放飛。相反的,沒人管就是大家管,大家管就是草木皆兵,各家銀行要不斷在自由銀行這個機制裡證明自身的信用與實力,這種情況下,胡亂發幣就是自尋死路。
放飛者會被審慎者砍掉翅膀,而不是反過來審慎者被放飛者牽絆得引頸上吊。2009 年美國茶黨運動就是一個案例:為什麼我一個本分工作、可靠做事的良好公民,要去為放飛自我、債台高築的次貸人口買單?給一個好的激勵機制,然後讓大家各自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才是公平的制度。虧錢,會激發人類的自相殘殺;不公,會觸動人類的殘殺高潮。
而且蘇格蘭的這一套金融銀行制度,除了製幣、換匯、借貸以外,也有商業票據和保險業務,已經與現代商業銀行提供的服務相差無幾。這就不能說像交子一樣,蘇格蘭去中心化實驗是一個幼稚園等級的解決方案。
蘇格蘭自由銀行實驗最美妙的地方,就在於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實驗。因為就在蘇格蘭的隔壁,有一個同宗、同源、同文化、同時代的控制組——英格蘭。英格蘭又恰好有一個各國央行的先驅——英格蘭銀行。而事實上大約從 1720~1840 年間,自由銀行體制之下的蘇格蘭幾乎不曾發生過金融危機,而央行體制的英格蘭,只能說是在金融週期裡乘風破浪、九死一生。1809 年到 1830 年之間,英格蘭共有三百家銀行關門,而同時蘇格蘭卻沒有任何一家銀行倒閉。
令人百思不解,央行不是維穩神器嗎?很簡單,本來鐵鍊鎖著所有的普通玩家,偏偏有一個是人民幣玩家——央行——有特權的鑰匙,時不時可以解開桎梏、放浪形骸;沒有人能夠砍掉央行的翅膀,他想 QE(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寬鬆)就 QE、他想發幣就發幣。自由市場、自由銀行制度肯定也會有其危機,會發生擠兌、流動性危機,也會有大銀行破產(詳見 Ayr Bank 破產案);自由市場肯定會有原生的問題,但是無論問題是什麼,顯然央行都不會是天命的答案。
既然央行的好壞是個有待商榷之事,那為什麼無論歐美或是蘇俄,從天主、清真再到馬克思主義,都信奉中央銀行能夠強身健體?無論是公行還是私行(比如美國聯準會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卡特爾),央行就像青苔滿佈如草蓆般長滿了我們的星球,如影隨形、政府標配。你見過不附贈央行的政府?威權主義愛央行,威權主義愛凱因斯(Keynes)。
而凱因斯,作為一個身高近兩米的同志愛好者,是央行存在合理性的精神依據。在看待經濟體這個問題上,凱因斯並不像他的性向那樣 “什麼都行”——他明確表示市場不行。他認為經濟體不是一個可以不斷自我修復的細胞,而更像一關超級瑪麗(Super Mario),你可以蹦躂著吃蘑菇變大變小,然而一旦掉到坑裡,就難以回來。此時就是所謂的 “缺乏有效需求”,為了刺激需求,加大政府開支,是為凱因斯主義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也是一樣,市場缺錢,就讓央行的印鈔機來大水漫灌(或者在美國聯準會的案例裡,就是聯邦基金利率、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這三個手段),於是流動性的問題就被暫時解決了;當然長遠而言,問題並不是被解決的,永遠都是因為被拖延。當然凱因斯對此並不以為意,他說過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從長遠而言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因此拖延問題等於解決問題,只要你把問題拖過了你的壽命。”
所以假設你是 “決策者”,你不愛央行你愛誰?畢竟央行給了你無上的實權。為什麼央行要出來主持大局?因為很簡單,被管轄的人們身上有太多動物本能。凱因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的 “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是一種更傾向於 “作為” 而非 “不作為” 的衝動,或者說是一種 “本能的樂觀”,而非 “理性的經濟期望”,所以動物本能讓整個週期顯得毫無週期可循。凱因斯得出結論:“所以經濟沒有政府根本不行,你見過一群呆羊缺得了牧羊人嗎?動物啊,我們都是畜生。”
是不是有一點計劃經濟的苗頭?但是千萬別誤會,凱因斯並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反倒是個人主義的先驅。凱因斯認為人可以英勇地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哈耶克(Hayek)就比較悲觀,他認為我們被經濟規律(市場規律)所主宰。橫加干預,只能枉然(或者更壞)。凱因斯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甚至連溫和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發源於英國的一種循序漸進的民主社會主義)都算不上;凱因斯一直都是一個凱因斯主義者。
當然凱因斯凱大師一定不在意自己的派別與主義,也不會在意別人給他貼標籤。他是那種在經濟學考試上考個鴨蛋也無所謂的人(真實事件),大師內心肯定是鎮定的。
我們說了央行邏輯的精神領袖是凱因斯,但是肯定有很多人要群起而滅之。比如凱因斯的真命天子——哈耶克。在此筆者倒想提一提許小年老師的觀點:“市場的不完美是公認,但難道政府的不完美就不公認?” 同樣的,用不完美的央行來試圖讓不完美的市場完美起來,邏輯上不是有坑?
所以央行的好壞,事後才知道。2008 年我們的經濟斷崖式崩潰,本來市場有一次自我糾正的機會,結果迎來了四兆人民幣。許小年認為,我們在 2008 年 “浪費了一次危機”,當時中國經濟的崩潰本來或許是個契機(結構性調整),但是四兆的大水,讓契機變劫機,劫機最後導致了多年以後中國經濟不得不迎來的墜機。我們無非就是拖延了問題,而非解決了問題,難道這就是央行存在的全部意義?
1930 年開始的大蕭條,許多人以為是羅斯福新政,幫美國走出了泥潭,事實上或許正是因為羅斯福新政才導致了曠日持久的泥潭;而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美國貨幣史》裡也論證了,美國聯準會錯誤的貨幣政策才是大蕭條的一個主因。
所以無論金本位是多麼野蠻的遺跡,中央銀行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還是那句話,拖延問題是否等於解決問題?確實,長期來看我們都要死,但萬一我沒能把問題拖到死呢?那麼自作自受的我們,是不是要顫顫巍巍地總結人生:出來混,遲早要還。
《雪球》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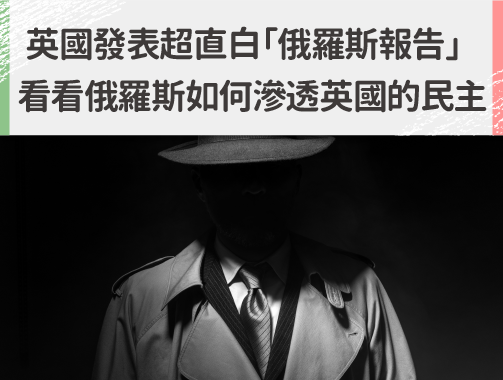


從日本泡沫化的罪與罰-看中國的經濟泡沫-_-.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