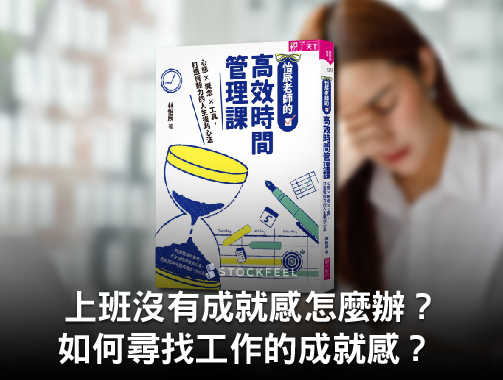幾千萬年前,人類誕生,但茹毛飲血的時代,人類難以被稱其為人。當人類第一次擁有了智慧之時,當人類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時,我們才覺得,人類誕生了。
我們從未放棄過追逐意義。
歷史上被稱為軸心時代的時期,誕生了無數先賢,中國的孔子、老子、墨子,百家爭鳴,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百花齊放,他們用著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方式,追問著人的意義,世界的本源,於是建立起了我們今天幾乎所有的哲學、宗教、科學、藝術的根基。
人類在追逐意義的過程中,創造出了文明。
但文明發展到今天,我們似乎丟失了對意義的追尋,整個社會,陷入了一場“意義危機”——很多人找不到人生的目標和意義,變得麻木不仁,過得像行屍走肉一般。
意義不會源於所做的事,而是來自於某個超越性的世界,可以將其稱之為源頭世界。
所以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必須在自己的現象世界之外,建立源頭世界作為根基。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覺得內心痛苦,就是因為與源頭世界失聯。而與源頭連接的方法,就是“臨在當下”。
一、人類兩大千古難題
人類幾千年以來,有兩個未解之謎,無數哲學家、思想家都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解答這兩個問題裡去,但很遺憾,到現在為止這兩個問題都沒得到很好的解答。
第一個問題是認識世界,第二個問題是認識自己。其實還有隱含的第三個問題,那就是我和世界的關係。由於前兩個問題都沒解決,第三個問題也就沒得到解決。
先來看認識世界。對應著哲學裡的本體論,古希臘關於本體論的思維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叫“原子論”,認為世界是由特別細微、不可再分的原子,以及原子周圍的虛空所組成。
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其實事物不是本質,事物之間的關係才是本質,這些關係可以用一些理念表達出來,這被稱為“理念論”。
後來,原子論和理念論直接推動了自然科學的進步,一脈是對最小單元的追索,物理學家一直追到了電子、夸克等;另一脈是對世界萬物至理的追問。
然而,這兩脈都遇到了攔路虎,導致無法繼續追問下去。
原子論這一脈遇到了海森堡,海森堡是量子力學方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提出了“測不准原理”,我們原以為把一個事物的最小單元找到後,了解了最小單元,就能了解這種物質,但海森堡認為,最小單元的位置和動能不可同時被確定——如果你知道最小單元所在的位置,就永遠不知道它的速度;如果知道它的速度,就永遠不知道它在哪。這等於給原子論這一脈“判了死刑”。
理念論這一脈則遇到了哥德爾,他提出了“不完備性定理”,從數學上證明,在任何人類理性系統之外,總有一個“搗亂分子”跟這個系統是不相容的,如果想把“搗亂分子”包含進來,原有體系的自洽性就崩潰了。也就是說,人類的理性有不可克服的結構性缺陷,等於給理念論這一脈“判了死刑”。
所以,到今天為止,認識世界這道題原則上是不可解的。大哲學家康德也只好宣布:“物自體”不可知。意思是說,我們只能了解現象界,而不能了解世界的本質是什麼。
你可能會說,我們有那麼多科學定律,都不能用來認識世界嗎?可以說,幾乎所有定律都是關於世界的資訊,相當於給世界拍了張照片,但並不是世界本身。這就導致我們對幾乎所有重大問題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舉個例子,愛因斯坦提出“光速不變”作為狹義相對論的基本假設,但為什麼光速不變?愛因斯坦也不知道。為什麼任何物體,甚至連資訊的運動速度都不超過光速?愛因斯坦也不知道。光在宇宙中為什麼如此重要,甚至重要程度超過時間和空間?也沒人知道。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如果我們只是通過研究系統的現象來研究這個系統,就無法真正了解這個系統。所以,我們如果想了解世界是什麼,就必須先了解世界的源頭是什麼。
二、探尋世界的源頭
世界有沒有源頭,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他們認為世界的源頭是存在的,而且他們表達存在的那個詞很奇怪,不是現象存在的“existence”,而是“being”,表達的是本體性的存在。
回答世界源頭這個問題的集大成者是柏拉圖,他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隱喻”,認為我們實際生活在一個洞穴裡,每個人都被鐐銬鎖著,眼睛只能往前看,而我們看到的任何東西,其實都是身後事物在陽光照射下投射到牆上的影子而已,柏拉圖用太陽代表真理,太陽間接的投射影代表人類的知識。
如果想了解真理,就必須從洞穴裡爬出來,到一個新的世界。柏拉圖稱外面的世界為理念世界,洞穴裡是現象世界。
言外之意,柏拉圖認為我們的世界之外有一個真正的世界,即理念世界,這是不變的本體,我們這個世界是由理念世界生髮出來的,只有了解了理念世界,才能了解現象世界。
如果我們把尺度放大一些就會發現,柏拉圖所說的兩個世界的關係,與老子所說的“道”在結構上幾乎完全一致。老子認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我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假如把天地理解為現象世界,“道”就是現象世界的源頭,所以老子相信現象世界有源頭。
幾千年來,對於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很多人並不認同,就連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都不接受,拉斐爾的《雅典學院》畫幅中間就是他們師徒兩人,柏拉圖用手指著天,認為世界的源頭在理念世界,而亞里士多德則用手指著地,認為世界的本質就是世界本身。
接下來,我們可以沿著柏拉圖的思路嘗試著進行思考,不論正確與否,都會讓我們的心胸和視野變得開闊。
如果想研究源頭,有三個問題避不開:
- 這個世界有沒有源頭?
- 如果有源頭,是一個源頭還是多個源頭?
- 如果有源頭,它有什麼特徵?
首先是世界有沒有源頭。
這裡,我們先來看宇宙是否存在源頭。
如果我們相信奇點大爆炸,就表明我們相信宇宙是有源頭的,宇宙的源頭就是奇點,奇點是什麼?沒人知道,但所有科學家都承認奇點的存在。
同理,假如把現象世界當作我們可感知、可想像到的最大宇宙,也一定存在源頭。那如果世界有源頭,是一個還是多個源頭?
談到源頭問題必須先解決一個悖論:源頭自己有沒有源頭?比如我們說現象世界來自於理念世界,然後立刻可以問一個問題:誰“創造”了理念世界?
我們可以說有一個更高的系統創造了理念世界,但問題又來了:更高的系統又是怎麼來的呢?如此類推下去,其實是無限遞歸,沒有意義的。所以為了避免這種現象,必須在有限步驟之內有一個到此為止的絕對源頭,這個絕對源頭符合一個法則,是我們解釋的關鍵,叫做“自指性”。
什麼是自指性呢?
簡單來講,自指性就是自己創造自己,自己複製自己,自己繁殖自己的特性。這裡不展開講了,有興趣可以去看一本書叫《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
比如,基因就具備自指性,基因決定了蛋白質的繁殖、解碼和解釋,但誰決定基因自己的遺傳代碼呢?基因自己。
我們前面提到的哥德爾,他在研究不完備性定理時用的就是自指性,圖靈看了哥德爾解這道題之後,也用自指性解了另外一道題。馮·諾依曼臨死前的最後一個研究就是機器能不能自複制,他用自指性來解釋機器可以自複制,這也是今天AI的一個大問題。
所以理念世界創造了現象世界,更高一個級別的系統創造了理念世界,但一定會有一個絕對源頭,自己創造了自己,它具備自指性。
但這個模型還是太複雜了,我們可以取一個極簡的模型,也就是說,理念世界創造了現象世界,理念世界具備自指性,創造了自己,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源頭具備自指性,那接下來的問題是有一個源頭還是多個源頭?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比如邏輯裡講因果律,任何事物都有原因,原因也有原因,但這個過程不能無限下去,必須有個第一因,那第一因是一個因還是多個因?第一因必須是唯一因。所以為什麼說“一”這麼重要?因為“一”既是第一,又是唯一。如果源頭不是唯一因,當然也就不是第一因了,肯定還有別的因,就不能到此為止。真正的第一因生髮出了所有的一切,是最後一個,才能提供絕對性的力量。
所以,絕對源頭是一個源頭。
這個源頭具備什麼特性呢?
這個特性可以被稱為“絕對創造性”,這個詞非常重要,源頭創造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是絕對的創造者。也就是說,凡是被創造之物都不是源頭,都不是理念世界。
我們可以來猜想一下源頭的特徵,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源頭是無限的。如果源頭不是無限,而是有限,那就不是源頭了,所以源頭一定是無限的,源頭之外什麼都沒有,可以說是“其大無外”。
第二,源頭是“ 0 ”。由於源頭創造了一切,所有被創造之物都不在源頭,源頭沒有一絲被創造性,可以說“其小無內”。源頭甚至沒有時間和空間,因為時間和空間也都產生於奇點大爆炸,而所有被創造之物——包括時間和空間,都不在源頭世界。
第三,源頭是“ 1 ”。有且僅有一個源頭,它本身沒有二元性,有人稱其為“Ultimate One”。
“無限”“ 0 ”“ 1 ”這三個特性合起來,就是源頭的一元性。
現象世界跟源頭最大的區別就是現象世界一定是兩極化的,比如有主觀有客觀,有你有我。而源頭是一元性的,有且只有這一個整體,大到無限,小到沒有任何內容。
柏拉圖稱這個一元性的源頭為“理念世界”,如果用中文來表達,最接近的是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的“存在是一”。
可以說,“存在是一”是世界的源頭。
三、找到源頭才能認識自己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我的源頭是什麼?相信每個人更關心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其實不太關心世界的源頭是什麼,更關心我們自己是誰。
對於“我是誰”這個問題,哲學家笛卡爾的回答最為經典,我們最為熟悉的“我思故我在”其實就是笛卡爾在理性層面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
《莊子》中有個“莊周夢蝶”的寓言,笛卡爾也思考了類似的問題:怎麼才能證明我存在呢?現在的我,會不會是另外世界的“我”在做夢呢?會不會是某個人在我腦中植入了什麼東西,讓我看到眼前的一切呢?
於是,笛卡爾做了一個思想實驗,假設可能存在一個“邪惡騙子”,他可以把想法和知覺植入人腦中,所以你所看到的世界只是“邪惡騙子”在你腦中植入的想法而已,就像我們在《盜夢空間》《駭客帝國》中看到的橋段。
今天有人把笛卡爾稱為“虛擬現實理論之父”,但他的假想是有可能存在的,因為到今天為止,我們無法從邏輯上證明我們不是生活在“駭客帝國”裡。正如埃隆·馬斯克曾在一個訪談中提到,我們生活在真實世界的可能性只有億分之一。
笛卡爾希望藉助這個思想實驗探索什麼才是真實的存在,找到某個真實存在的東西,以此作為錨點,建立起人類的知識大廈,那知識大廈就必然是真實的。在絕望中,笛卡爾依然想找到根基,重建人類生活和信心的大廈,這種努力非常值得尊敬。
可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才是真正的存在呢?即便我們掐一下自己感到疼痛,但這種疼痛感也可能是“邪惡騙子”輸入給我們的。
笛卡爾認為,我們不能確定任何東西是否為真,甚至不能確定大腦中想的事情是否為真,但有一件事應該是真的,那就是我正在思考。也就是說,雖然思考的內容不能確定是真的,但思考的狀態一定是真的。如果我正在思考,那一個思考的主體必然是存在的,他把這個主體命名為“我”,所以他說出了那句震古爍今的話:我思故我在。這個推理是整個形而上學的第一性原理,非常重要。
但笛卡爾也遺留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思”和“我”的關係,他只證明了“我”的精神存在,不能證明“我”的身體存在。
後來有個哲學家就沿著笛卡爾的思路往下證明,認為笛卡爾只是證明了精神是存在的,並不能證明這個世界存在,於是認為所謂的世界就是我感知中的世界,只有精神性的存在。雖然這話聽起來很荒謬,但從純邏輯角度卻無法否定。
所以,笛卡爾的證明是有悖論的,根本原因在於他沒有回答源頭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意識的源頭是什麼?心智思考背後還有沒有更高的意識?他沒回答,他把心智和思考定義為意識的最高級了。
二是他沒有回答“我”背後還有沒有“我”,換句話說就是,笛卡爾只是回答了“我是誰”,而沒有回答“我的源頭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同樣可以試著思考一下笛卡爾沒有回答的兩個源頭問題。
首先,思考背後還有沒有更高級的意識狀態?
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有一個隱含假設,他說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就是我正在思考,這個隱含假設是我知道我正在思考,這其實有個巨大的邏輯問題:你怎麼知道你正在思考?
舉個例子,假如你在做夢,你什麼時候知道你在做夢呢?就是當你醒過來的時候。如果思考背後沒有別的意識狀態了,只有思考這個終極狀態,思考怎麼能知道你在思考呢?
笛卡爾的我知道我正在思考,一定意味著有一個比思考更高級的意識層次存在,它知道你在思考。所以,笛卡爾的“我思”不能證明出“我在”,只能證明出有一個比“思”更高的意識狀態存在。這個更高的意識狀態是什麼呢?
喬達摩其實也提到過那個更高級的意識狀態,他稱之為“覺性意識”,我覺知到我正在思考,肯定得有某個覺知,所以證明有“覺”的存在。所以,“我思故覺在”。
但這裡依然有一個隱含的邏輯問題:你怎麼知道你正在覺知?
為了避免無限遞歸,同樣可以用自指性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取一個最簡模型,認為“覺”是一元性的,知道自己正在思考。
為什麼“思”不能知道自己在思考呢?
因為我們可以用“思”來認知世界,但無法認知“思”本身。就像我們可以用邏輯來思考這個世界,但無法用邏輯去思考邏輯本身。
這個悖論是人類認知的最大悖論,正所謂“能切之刀切不了自己,能看之眼看不到自身,所感知者無法去感知”,王東岳將其稱為“形而上學禁閉”。
“覺”這個層次出來以後,有一個巨大的優點,那就是不但能覺知對象,還能覺知自己。所以,“覺”是“絕對能知”的——所有可以被認知的對像都不是“覺”本身。
同樣,“覺”也有三個特徵:
一是沒有內容。一旦有概念、有定義、有思維、有語言、有思想、有內容,它就成了覺知的對象了,所以“覺”內部沒有任何內容。
從邏輯上推,覺性意識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形式,而不是意識內容。我們的思想是有內容的,而覺性意識是內容的所在,是內容周圍的空間。
二是無限。 “覺”的外部沒有二元性,它是絕對能知。
三是有且僅有一個源頭。
這三個特徵合起來就是“覺”和“思”的最大不同——“覺”是一元性的,它自己本身是絕對主體,沒有任何客體性質存在。
我們思想的最大特徵就是二元性,舉個例子,我們的語言就是兩極化的,比如“我在講課”,“我”是一個主體,“講課”是一個動詞;“我和你”也是兩極化的。所以大家把理性的邏輯理解為一把刀,一旦用邏輯就把物體切為二分。
仿照“存在是一”,我們可以將這個一元性的意識稱之為“覺性是一”,就是說覺性一定是存在的,而且是一元性存在。
以上,我們回答了第一個關鍵問題,即意識背後是有源頭的。那麼,第二個關鍵問題才會出來:如果意識有源頭,“我”的源頭是什麼?
在笛卡爾的證明里,“我”是思考的主體,但前面我們也提到,笛卡爾的“思我”其實是思考的對象,而不是主體,喬達摩的“覺我”才是“我”的源頭。
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覺故我在”。由於“覺”本身俱備自指性,所以跟“覺”對應的“我”才是源頭性的我。
我們證明了思維有個源頭,我也有個源頭,接著就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兩個源頭是什麼關係?
在二元性思維里,“我”和“思”是兩回事。但在一元性意識裡,“我”不能是“覺”的對象,“覺”也不能是“我”的對象,也就是說,“覺”和“我”不能互為對象,所以“我”和“覺”是什麼關係呢?
從邏輯上只能推出“我”就是“覺”,即“我就是我的覺性意識,我的覺性意識就是我”,這是在二元思維語境下的同義反复,根據奧卡姆剃刀原則,完全可以去掉其中一個概念,去掉誰?只能去掉“我”,“我”是一個主體性的概念,“覺”是去不掉的,因為“覺”一定存在。
此處證明“我”不是一個獨立性的存在,獨立存在的是“覺”,它既是一種思維方式,又是主體。我們也就明白佛教里為什麼說“無私、無念、無我”了,因為“覺”就是無我的,只剩下覺性意識本身,它就是“我”,它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永恆存在。
所以,“覺性是一”是每個人的源頭,《新世界》這本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寫得很棒:世上只有一個絕對真理,其他的真理都是從它衍生出來的。當你能夠找到那個真理的時候,你的行動將會和它一致。真理與你的本質是無法分開的。是的,你就是真理。如果你只在他處尋求,那麼每一次都會被誤導。你原本即是的那個本體,就是真理。
四、全部宇宙都在我的里面
我們前面分析了“理念世界”和“覺性智慧”,它們兩者之間是什麼關係?也就是世界的源頭和我的源頭是什麼關係?
從邏輯上來講,個體的覺性存在和宇宙本體不可能是兩個存在,因為如果是這樣,就違反了一元性。即使是一個很小的“我”的本體和很大的宇宙本體,更像是包含關係,我的本體是宇宙本體的一部分,也是兩極化的,哪怕只有萬分之一,也跟其他部分形成二元分立。
那就只剩下一個答案了,即個體的覺性存在和整個宇宙的本體存在是同一個存在。
這是一個非常讓人驚訝的結論,我如此之渺小,宇宙如此之浩大,怎麼是同一個存在呢?
我們都知道宇宙有多大,地球是太陽系的 8 個行星之一,銀河系裡有 3000 億顆與太陽類似的恆星,整個宇宙裡有 3000 億個和銀河系類似的星系。但似乎,只有一個答案——“我的源頭就是宇宙的源頭”,完全不可想像。
什麼機制能幫助我們解釋我和宇宙的關係?答案是分形。正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從一個微小的“我”切入進去,就是整個宇宙。而且這不是常規意義上的分形,是絕對分形——切入進去之後不是一個新的世界,還是原來那個整體。這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因為我們有空間的概念,而那裡沒有空間。
所以本體存在於無限大等於無限小的地方,我看過這樣一段話:對你來說,宇宙好像在外面。它不是。事實上它在你的里面。我們每一個人都包含著全部,可以被永無止境的“放大”,全部宇宙都在我的里邊。
此處所說的“宇宙”不是現象世界的宇宙,而是宇宙的源頭。 “我”也不是思想性的我,而是我的覺性意識的源頭。所以整個理念世界不在外面,而在裡面。
宋朝心學開創者陸九淵說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
五、“臨在當下”是通往源頭的途徑
我們說世界的本體和我的本我是同一個源頭,如果這樣的源頭存在,我們如何通往這個源頭呢?
通往源頭的路有千萬條,把所有的路拿來研究,發現有一個堡壘是必須攻克的,即“No Mind”,也就是“無念”,超越心智、超越大腦、超越思想,然後就能進入到覺性智慧的狀態。
對於你來說,只需在通往源頭的路中選擇一條最適合的就行,我覺得有一條路很通用,無論你去專業修行,還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都可以學習,這條路就是“臨在當下”。
什麼叫“當下”?這個詞看起來非常微不足道,而且被用濫了,我們一般認為它是個時間概念,事實它不是一個時間概念。
時間到底是什麼?它真的存在嗎?你猛然一聽這句話,肯定覺得不可思議。
事實上,科學研究有個基礎的方式叫經驗主義,認為只有建立在感知之上的經驗,才能構成知識。休謨是英國經驗主義的先驅,他說,我們只能感知每一個時刻發生的事,卻無法直接感知到時間本身。因此,時間並不存在。
想想看,歷史學裡有很多大事記,某年某月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心裡會把這些點畫成一條線。但這條線我們能感受到嗎?它看不見,摸不著,什麼儀器也測量不到。
即便鐘錶上也不是真實的時間。我們把地球繞太陽一周定義為一年,地球自轉一周定義為一天,大家根據這個約定了時間,並且做成鐘錶,也就是說,鐘錶裡的時間只是地球運動的標識,不是真實的存在。
可是我們卻以為有一個時間存在,那是我們的心理時間,康德稱之為“先天直觀形式”,意思是時間客觀不存在,是內置到我們心中的。
所以,時間根本不存在,而且對於每個人而言,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只有當下。
請你想一下,什麼叫過去?過去是你此時此刻的回憶,也就是說,你只能直接感觸到此時此刻對過去的回憶,根本無法直接感受到過去。什麼叫未來?未來是你此時此刻的想像,所以未來也發生在此時此刻,發生在當下。
所以《新世界》這本書裡說,到處都有時間確實存在的間接證據。比如,你見到小時候的發小變得很蒼老,你感嘆時間是把殺豬刀,認為是時間讓他發生了變化。但你找不到任何時間存在的直接證據,你從未經歷過時間本身,如果需要直接證據才能證明時間存在的話,那麼,時間就是不存在的,而當下則永遠存在。
但是,在我們心中,通常都把過去和未來看得很重,恰恰沒有當下。當下通常被我們當作未來的一塊踏腳石,是實現未來目標的工具和過程。但如果你把生命的“一”放在未來,就會出現一種“未來悖論”:你說,等我實現了未來的某個目標,我就幸福了,當你實現這個目標之後,又會繼續想一個未來的目標,之後還會不斷有下一個目標。
也就是說,你會永遠都在轉向,就像一頭驢,主人為了讓它拉磨,在它前面放一個胡蘿蔔,驢拼命追胡蘿蔔,不斷轉向,卻永遠都追不上。
各位想想,是不是這樣?我們以前一直認為最重要的是高三,認為考上好大學就幸福了;但上大學後發現,大城市如此繁華,但沒錢,認為工作賺錢了就會幸福;工作後卻遇到一個糟糕的老闆,覺得當了老闆,能掌控自己的命運,就會幸福了,所以就去創業;創業後發現,原來比打工還苦,等到公司上市就幸福了。
中國現在的上市公司越來越多,但有幾個上市公司的老闆是幸福的。每個人都被公司綁架了,開始想什麼時候把公司賣掉,我就幸福了……
所以,未來永遠是站在當下投射未來,我們永遠抓不到未來,這是時間給我們最大的困擾。
接下來,我們再從科學的角度拆分一下時間。愛因斯坦說,時間是光速的函數。如果我們想搞明白時間,得先明白光是怎麼運動的。
光運動時並不是每個空間都經過,它其實是從一個地方消失,到另一個地方重新出現,可以看成“跳著走”,中間極小的時間裡是沒有光的,這段時間可能只有 10 的 42 次方分之一秒,也有人說是 10 的 28 次方分之一秒。
什麼叫當下?
當下是極微小的光和光之間的那條縫,但是無限小等於無限大,如果我們從這個縫切下去,就能連接上源頭。也就是說,當下不是時間,而是時間和時間之間那條縫。
所以,那一瞬間才是你跟源頭連接的地方。 《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中的一段話特別棒:在認知一個物體之前,必然有一種非知識的意識,斐德洛稱之為良質的意識。在你看到一棵樹之後,你才意識到你看到了一棵樹。在你“看到”的一剎那以及“意識”到的一剎那之間,有一小段時間。
這段時間就是當下。
我們換個極大的尺度來理解,你晚上看星星,你此刻看到的星星並不是現在的,而可能是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年之前的星星,已經都是過去了。無限小也一樣,我們看到一個事物一剎那之後,才形成對這個事物的意識,在一剎那的當下,我們是在體驗事物,之後才形成意識,意識相當於為看到的事物拍了張相片,而且這張相片不是一剎那時候的相片,而是一剎那之前的相片,是過去了。
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現實,只有一剎那的當下。
時間禁錮了我們和源頭世界的連接,假如我們想從中越獄,需要找一個漏洞,這個漏洞就是時間居然有條縫,只要你保持臨在切入進去,把縫變得越來越寬,有一天就會突然擊穿閾值,跟源頭連上了。我稱這種跟源頭連接的方式為“ 90 度革命”。
今天我們基本上都在時間的水平線上奔跑,追求更多更快,幾乎很少有人告訴你,真正的力量不在未來,而在當下,“臨在當下”這四個字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
六、靈感流淌是最美妙的狀態
我們怎樣抓住當下?
就是此時、此地、此事,達到一種“No Mind”的狀態講一個故事,有位禪師開悟了,小和尚就問禪師說,你開悟前和開悟後有什麼區別?禪師說,我開悟前砍柴、擔水,開悟後砍柴、擔水。小和尚接著問,那不是一樣的嗎,怎麼能叫開悟?禪師回答說,我開悟前砍柴的時候想著擔水,擔水的時候想著砍柴,我開悟後,砍柴的時候想著砍柴,擔水的時候想著擔水。
你要集中於此時、此地、此事,忘掉過去,忘掉未來,怕的就是你在工作的時候,想著通過這份工作賺一筆錢,然後退休去享受生活。工作時心在別的地方,既做不好工作,又不是修行的狀態。
有一項運動最能體現臨在當下的狀態,那就是徒手攀岩。徒手攀岩時,你不能想昨天干什麼了,不能想攀岩後就出名了、有錢了,甚至連你的前一個動作也不能想,全部精力必須在當下這個動作上,把它當做一生中最重要的,因為只要這個動作做錯了,命就沒了。
而且徒手攀岩時你都不能緊張、焦慮,不能過度思考,否則就會過度消耗。攀岩者的每一步都踩在死神邊上,我們有時候都不敢看,但你看他自己的狀態,非常瀟灑,跟跳舞一樣。
假如用一個數學公式來表達臨在當下,那就是分形學裡的“Z⇄Z²+C”,帶入一個“Z”,得到一個新的“Z”,循環反复,臨在當下就是“⇄”這個符號,不是結果,是過程。
可能很多人會擔心,如果只是此時、此地、此事,會不會影響我的業務?會不會讓我喪失遠大的理想?
恰恰相反,讓自己達到“No Mind”的狀態,不是放棄努力,而是把自己託付給一個更加宏大的力量和智慧。擊穿閾值之後連接源頭,獲得的力量和智慧遠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對於我們東方人來說,跟“臨在當下”最接近的原型就是禪。
鈴木大拙是第一個把東方的禪推薦給西方的人,他認為,禪極具開放性精神,被引入什麼活動都可以,在日本,禪就被引入了各行各業,比如劍術加禪變成武士道,弓箭加禪變成弓道,繪畫加禪變成畫道,茶藝加禪變成茶道。很多技藝在加入禪的精神之後,都發生了奇怪的事——技藝本身變得不是目的,而成為通往禪的路。
德國哲學家赫立格爾寫了一本書叫《弓和禪》,用非常寫實的手法描寫了他在日本學習射箭的過程。
赫立格爾是德國康德學派的哲學家,非常理性,又對東方的神秘主義特別感興趣。藉著去日本做哲學老師的機會,他接觸了禪學,他把《弓和禪》當做了他學禪的一個實驗性的描述。
赫立格爾拜的老師是弓道大師阿波研造,據說阿波研造是一個百發百中的神箭手,但他沒有直接跟禪宗大師接觸過的經歷,他的開悟是通過射箭來得到的。
他學了好多年之後終於悟到了弓道的精髓,他說,什麼都不要想,你自己只需要把弓拉到最圓滿、最成熟的狀態,這時箭就會不經意間自動射出,直奔靶心。
要想更好地抓住當下,達到“No Mind”的狀態,還要注重寂靜。時間在我們身上的體現就是當下,而空間對應的是寂靜。
這裡的寂靜不是安靜,而是事物周圍的留白,空間背後的空間。假如你完全進入到一種沒有思維的內在空間,你內在無限深的空間就會跟外在無限廣的空間產生共鳴。
寂靜其實是人極力抗拒的,通常我們自己呆著的時候,會覺得無聊,甚至恐懼,彷彿跟世界失去了聯繫,尤其是我們年輕的時候,總希望能參加各種聚會,在觥籌交錯的熱鬧中尋找自己。
你跟朋友一起吃飯、喝酒或喝茶,你們的狀態是什麼樣的?會說個不休,覺得無話不談才是朋友間的最高狀態,一旦你說完停下來了,我就得接上去,如果中間沒人說話,就有點冷場。
而靈魂伴侶是什麼樣的?就是你們在一起待一天,哪怕一句話都不說,也不覺得尷尬,儘管一句話都不說,實際上所有的話都說了。
寂靜很好的範例是茶道精神,它的美在於單純而寧靜的品味,儀式化的飲茶方式目的在於成為自己心靈的主宰,換句話說,茶道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有所醒覺。在一個很小、很簡單的地方,整個過程中唯一能聽見的聲音或許只有水壺裡沸騰的水聲,或者屋外的風聲,透過這一小碗茶,主客之間的藩籬消失殆盡,泡茶的主人和旁觀的客人在不知不覺中化為一體,共享寧靜祥和,雖然什麼都沒說,但我和你,我和環境合而為一。
禪加上茶是茶道,禪加上建築就是建築之道,日本建築中有一種風格叫“Ma”,指的是空間,也就是空間背後有空間,讓你感受到內在的空間。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沉默,如果我們說話說到一半突然暫停,可能會覺得不安,但日本人覺得這樣的空白和停頓也同樣飽滿,充滿意義。
在負空間的建築裡,隔板能一層一層滑動收合,將空間打開,即便是外牆也能行動,產生出一種連續空間的效果。
這才是“Ma”之美、寂靜之美、簡約之美,寂靜之美不是事物,是事物周圍的空間。
反思一下,我們的生活中有多少時間是接近留白的,有多少時間是留給安靜下來的自己的?杜克大學有一個教授研究聲音對人類神經系統的影響,他對比了絕對安靜和莫扎特的音樂在人腦中產生的效應,結果發現,絕對安靜比音樂更能促進腦細胞的發育。科學家的研究還發現,每天安靜兩小時,就會促進大腦中海馬區的發展。
《新世界》裡有一段話寫到了寂靜之美:
靜默的確是空間的另一種表達。在生活中碰到靜默的時候有意識地覺知它,這樣可以使我們與內在那個無形和永恆的向度聯結,那個向度是超越思想和小我的。
在靜默之中,你在本質上以及更深的層面上,是最接近自己的。在靜默中,你是原來的你,在暫時承繼了這具肉體和心理形式而被稱作一個“人”之前的那個你。
如果能臨在於當下,臨在於寂靜,就能超越思維,產生覺性智慧。
覺性智慧在我們的工作生活中可以用“靈感”這個詞來表達,我們通常把靈感理解成思想裡的靈光乍現,突然有了個好主意,突然冒出了個好創意。其實不然,靈感是正常狀態,只不過被遮蔽住了,如果你能去除那些遮蔽物,讓它自然流淌出來,那才是最美妙的一種意識狀態,我稱之為“靈感流淌”。
在《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這本書中,主人公在一所大學裡教修辭學,佈置了一個題目,寫一篇 500 字的文章。班裡有個女生才華平平,她想寫一篇關於美國的文章,寫不出來,向老師求教。老師說,題目太大了,你不要用 500 字寫美國,你可以用 500 字寫一下我們的城市。
第二天那個學生還是沒寫出來,老師說你再縮小一點,把學校門口的街道寫出來。女學生還是愁眉苦臉,寫不出來。老師急了,讓她寫學校對面的歌劇院,女同學還是寫不出來。老師實在太憤怒了,親自把她領到歌劇院對面,讓她從歌劇院正面牆壁左邊最下面的第一塊磚開始寫。
結果到了第二天,這個學生不是帶來一篇 500 字的文章,而是帶來了一篇 5000 字的文章。
我想這個練習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靈感流淌的狀態不是偶然得來的,而是訓練出來的。
要想實現靈感流淌的狀態,既要有基礎性動作的訓練,又要通過臨在當下和寂靜留白把思維清空,達到“No Mind”的狀態,兩件事情加起來,你所做的事情就會有更高的質量。
《虎嗅》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