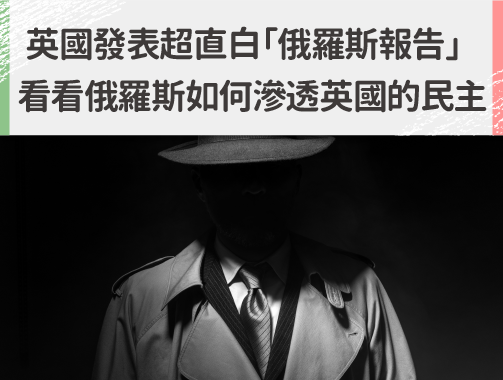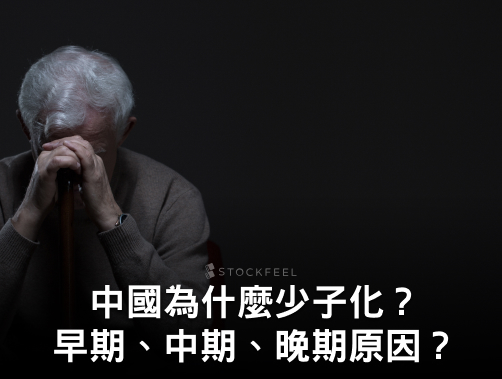在當今的中東地區,伊朗和以色列這兩個國家水火不容,伊朗前總統內賈德曾多次聲稱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以色列也時常發射導彈打擊伊朗在敘利亞的軍事目標。出於意識形態差異、地緣政治利益爭奪和國家安全的需要,雙方的關係惡劣也在情理之中。但奇怪的是,當前伊朗境內竟然生活著 2.5 萬名猶太人,歷史上這一數字更是高達 10 萬人。更出人意料的是,對這些少數族裔伊朗政府也特殊照顧,使他們過著和當地波斯人一樣的生活。這背後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嗎?
實際上,早在公元前 6 世紀,猶太人就大規模地出現在了波斯人的土地上。波斯曾經是猶太人嚮往定居的地方。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倫帝國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了猶太王國之後,便將大批民眾、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員擄往巴比倫,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巴比倫之囚”。猶太人飽受苦難的巴比倫之囚時代,已經成為凝聚猶太人認同感的重要歷史記憶。
猶太人東進避難
由於無法忍受巴比倫人的殘酷虐待,大批猶太人就因地理上的便利向東進入波斯境內避難。直到幾十年後波斯帝國的興起,猶太人才改變了命運。崛起後的波斯帝國在居魯士大帝的領導下逐漸消滅了新巴比倫,並釋放了被關押的猶太人,讓他們重回約旦河流域的故土。居魯士大帝允許希伯來朝聖者返回並重建耶路撒冷(希伯來人是猶太人的祖先),但只有一些虔誠的猶太人回去了,更多人由於長期生活在這裡,並且考慮到波斯帝國寬容的民族政策,決定留下來定居於此。
事實證明,這些人的命運也比那些回去後不斷繼續被驅逐的同胞們好一些,即使在波斯伊斯蘭化之後,這裡的猶太人仍然得以生活在相對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下。波斯帝國內部的地區和民族差異巨大,所以只要表示臣服和繳納賦稅,帝國就不太乾預小群體的內部自治。而之後的阿拉伯帝國,面對的問題與波斯帝國類似。
就這樣,人口的成長隨著時間的增加,到了近代,伊朗境內的猶太人竟然有好幾萬。他們從不擔心歐洲的排猶浪潮,只要接受伊斯蘭教領導,按時繳納特殊的信仰稅,就可以保留猶太屬性,擁有自己的教堂甚至從政。德國猶太人在一戰中也大量參軍,他們與德國戰友也享有相同的榮譽,然而這仍然擋不住歐洲和德國頑固的反猶主義傳統,並在多年後發展為可怕的悲劇。
而 1926 年建立的巴列維王朝,則無疑是這一群體的黃金時代。因為在之前,伊朗猶太人還要考慮政府奉行的伊斯蘭教對他們的限制,而現在一切就都不是問題了。新國王堅持政教分離、世俗化和親西方的政策,並且廢除了對少數族群的歧視性法律條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成為伊朗社會的兩個宗教類型,完全是平等的。法拉·帕拉維是巴列維王朝的皇后還創立了伊朗第一所美國風格的大學,或許這個帝國被腐敗所纏繞,但也養出了自由開放的果實。
1948 年以色列國家建立之後,伊朗境內的猶太人生活的就更好了,這自然是伊朗和以色列結盟的結果。
 大衛·本·古里安 在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創辦人 西奧多·赫茲爾 的大型肖像下宣布獨立(圖片來自:Wikipedia @Rudi Weissenstein)
大衛·本·古里安 在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創辦人 西奧多·赫茲爾 的大型肖像下宣布獨立(圖片來自:Wikipedia @Rudi Weissenstein)
沒錯,伊朗曾經是以色列的堅定盟友,還曾有過動用國家武裝力量護航向以色列轉運原油的友好歷史。雖然看上去有些奇怪,但類似的思路在今天的海灣地緣格局中仍然能看出端倪。伊朗雖然在輿論場上處處針對以色列,但那主要是因為它嚴格的反美立場,伊朗長期以來真正的對手,是沙特,而非以色列。以色列誕生之初,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幾乎都欲除之,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伊朗也並非阿拉伯國家,而且,伊朗和以色列都有美國站台。伊朗與沙特在地緣利益上有爭奪海灣控制權的巨大衝突,在宗教上有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衝突,敵對關係極為明顯。相反以色列與伊朗並不接壤,而且猶太人與遜尼派的仇恨也顯而易見,暫時放下意識形態對立聯手並不奇怪。
波斯人在波斯灣並沒有占到優勢,大部分海域還是掌握在對岸的阿拉伯諸國手裡,而對伊拉克的影響力和對霍爾木茲的控制權,就成為波斯灣兩岸爭奪的焦點。而此時滯留伊朗的猶太人,也成為了巴列維國王的座上賓,生活在伊朗極為滋潤,甚至不願回到新建立的以色列國家。實權掌握在世俗的伊朗國王手中,伊斯蘭宗教領袖也只能聽國王的,作為少數派的猶太人因此獲得保護。
伊斯蘭革命的改變
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我們要一個由伊瑪目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政府!” 但宗教的伊瑪目終究不是神,也就逃不過人類的私慾,不管是國家製度還是宗教立意,教徒和群眾都只是被統治者。親美的巴列維政權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仇視美國、以色列的伊斯蘭政權。由於伊朗猶太人與巴列維政權關係的緊密,革命運動中有的人認為他們就是美國安插進來的間諜。
這使在伊朗境內的 8 萬猶太人惶惶不可終日,很多猶太人就此逃離伊朗,幾年後就只剩下 3 萬左右的猶太人了新生的伊朗政權好對付巴列維王朝的殘餘勢力,還要對付其背後的美國人,還要防范國內猶太人會不會里通外國,確實是給自己設置了很多敵人。即使如此,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也仍然是中東地區除以色列外猶太人口最多的國家。但革命成功之後,霍梅尼和他的追隨者們卻冷靜地處置了這些留下的猶太人。他們公佈的條件是,只要不威脅新的伊斯蘭國家,猶太人仍然可以享受伊朗公民的待遇。
伊朗猶太人也抓準時機向新政權表忠心, 1979 年 2 月 1 日,當霍梅尼回到伊朗時, 5 千名猶太人在首席大拉比尤迪亞·沙費特的帶領下,參與到了歡迎最高領袖的隊伍中,打出了“猶太人與穆斯林皆兄弟”的標語,在伊朗媒體的大力渲染下迅速傳遍全國。
 尤迪亞·沙費特會見以色列總統(圖片來自“Wikipedia @Reubenzadeh)
尤迪亞·沙費特會見以色列總統(圖片來自“Wikipedia @Reubenzadeh)
面子上做得很好看,釋放的善意已經足夠多了,秘密的監視和控制還是少不了的。比如在政治上一旦坐實境內猶太人與以色列官方或美國營接觸,就立刻投入監獄。 1979 年 5 月,伊朗猶太人領袖就被指控參與顛覆政權的活動而被處死。在經濟上,政府將大量猶太人資本收歸國營,據統計至少有 10 億美元之多。猶太人在伊朗只能從事一些小百貨之類的業務來維持生計,這使在巴列維時期強勢的猶太商業社區也快速衰落,經濟上的軟弱自然也對伊朗政府的決策起不到任何影響。
在生活上,政府嚴格限制猶太人外出遊玩和移民,在辦理手續時必須進行至少三個月的全方面審核。教育方面,直接插手猶太教育,要求猶太人必須開設伊斯蘭教的課程,讓學生學習波斯語。顯然,伊朗政府一直在力圖同化境內的猶太人,以維持新生政權的穩定。但預想中的激烈矛盾還是沒有出現,伊斯蘭政府在外交場上對以色列尖銳的攻擊,很少延續到境內的猶太公民身上,只要他們安分守己,普通的生活仍然可以保證。其實在伊朗政府看來,猶太人在其境內的存在是必要的,這相當於對外宣傳伊斯蘭政權的包容和友好,這十分有利於樹立新政權的良好國際形象。而且猶太人在伊朗長期生活形成的歷史文化聯繫也很難完全割斷,在生活和語言上已經完全和波斯人融為一體了。因此,就算在最強硬的總統內賈德在任期間,也公開宣稱要把國內猶太人當成本國公民看待。
政府來接也不願意離開伊朗
然而隨著伊朗核問題日益嚴重,美國以色列和伊朗關係越來越惡化,伊朗猶太人十分擔心自身的安危。如果以色列空襲伊朗的核設施,或者美國向伊朗開戰,伊朗政府會不會將他們扣押為人質呢?畢竟 1979 年的伊朗人質危機還耳熟能詳。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力渲染戰爭氛圍的以色列政府開始行動了,派遣情報機構摩薩德前往伊朗進行營救計劃,勸說猶太人早點回國,甚至給予巨額金錢誘惑其離開伊朗。走吧,回家吧,回到以色列吧!
但十幾年來只有不到 2 千猶太人坐著以色列提供的飛機離開了,大多數人選擇留下來。這是為什麼呢?首先,伊朗政府雖然高調宣布要摧毀以色列,但在國內的實際做法卻完全是保護這些猶太人,他們完全可以享受穩定的生活保障,並且可以堅持自己的信仰。為了在政府與伊朗猶太人間建立一個溝通的渠道,憲法甚至規定議會中必須為猶太人留一個議員席位。在德黑蘭大街上,也經常可以看到不戴面紗的猶太婦女。伊朗猶太學校也允許男女生混住一起接受教育,在猶太婚禮上甚至男人女人可以相擁跳舞,而這些權利連穆斯林都沒有。
其次,伊朗社會也完全將反以色列和反猶主義區分開來,一個猶太人說著一口流利的波斯語,並不會讓波斯人感到反感。而且由於大多數猶太人不從政,只從事一些中小型商業活動,對穆斯林商人產生不了多少威脅,院外的反對勢力也很小。再加上猶太人在伊朗找工作和結婚困難,很多穆斯林甚至有些同情這一群體。最後,這些猶太人擔心回到以色列之後,享受的待遇會變低。因為他們現在只會講波斯語和英語,完全不會講希伯來語,也習慣了伊朗伊斯蘭化的生活環境,回到以色列後還要另找工作,估計很難適應高度發達的以色列社會,還會受到以色列政府或多或少的監視。
而且伊朗猶太人也十分清楚以色列國內的猶太人也是分等級的,來自歐美國家的猶太人享受最高待遇,而來自非洲的猶太人社會地位並不高,比如埃塞爾比亞裔的“黑人猶太人”。有這樣的先例在,再推測一步,以色列政府對來自敵對國家的伊朗猶太人進行秘密觀察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伊朗猶太人的心態是很複雜的,他們對同族的以色列人有宗教認同感,但又捨不得離開自己世代居住的新家園。政治訴求更是十分尷尬,他們既要保持對伊朗政府的忠誠來換取現實利益,又不得不傾聽和支持海外猶太同胞發出的聲音。兩相矛盾中,這些猶太人逐漸變成了失聲的群體,安於現在的生活,過著悶聲發財的生活。
《雪球》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