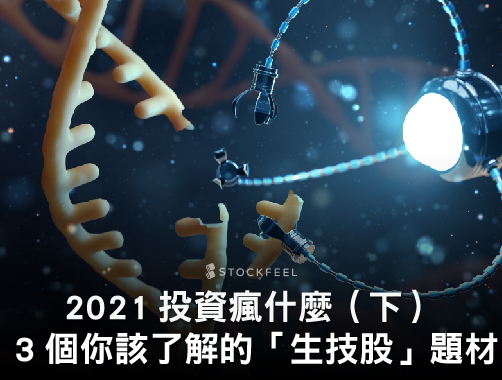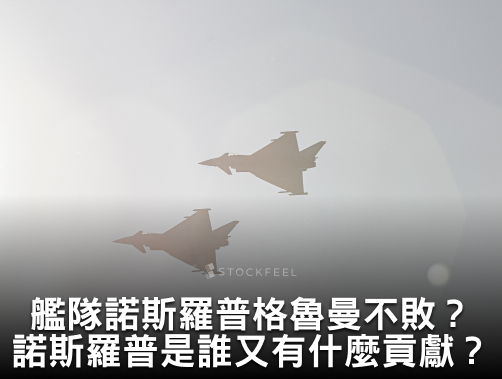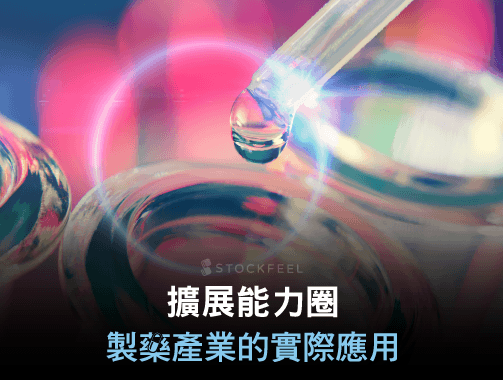40年前,一個年輕的科學家開創了基因工程(Genentech),一個年輕的投資人發現了它的價值。他們合夥創立的這家生物技術公司在4年內從40萬美元增長至3億美元,隨後統治生物製藥行業40年,市值從3億美元成長至500億美元。
這40年中,生物技術投資人苦苦尋覓,下一個基因工程在哪裡?40年成長100萬倍的傳奇在哪裡?現在他們似乎找到了些什麼,20億美元資金前仆後繼,生物技術融資記錄被一次次刷新,臨床結果即將揭曉。
兩代人物、兩個技術、兩個公司,一個已經開花結果,另一個才剛剛萌芽。他們的共同點是—都誕生在美國,不是歐洲,也不是日本。為何美國的生物技術如此繁榮?
上篇
Herbert Boyer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小鎮,父親和祖父都是當地的鐵路工人,由於祖父去世得早,父親為了維持生計13歲便輟學打工,母親上過高中。Boyer小時候非常喜歡足球、籃球、棒球,因為足球、棒球教練同時也教科學和數學,這激發了Boyer對科學的興趣。
Boyer高中畢業後進入聖文森特學院,開始學習醫學預科課程。很快他發現自己不想當醫生,而是想做科學研究,於是讀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生。1959年,24歲的Boyer結婚了,妻子是高中時認識的Marigrace Hensler,Hensler 畢業後便去Mellon Research Laboratories工作,Boyer在妻子工資的幫助下繼續讀研究所,1963年獲得PhD。
此時Boyer對細菌DNA產生了興趣,他決定去耶魯大學,在Edward A. Adelberg的實驗室繼續研究。這期間Boyer主要研究細菌質粒和限制酶,他認為限制酶可能成為非常有用的基因工程工具。1966年Boyer成為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助理教授,研究蛋白質如何識別特定的DNA序列。
1972年,Boyer在大腸桿菌中發現了一種限制酶,也就是後來著名的限制性核酸內切酶EcoRI。EcoRI能專一識別GAATTC序列,並在G和A之間切開產生黏性末端。在隨後的一次學術交流會上,Boyer認識了比他大一歲的Stanley Norman Cohen,Cohen當時正在研究細菌質粒。
1973年,Boyer與Cohen的合作開花結果,他們的論文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發表,利用Boyer發現的限制性核酸內切酶EcoRI,成功在Cohen分離的質粒pSC101上實現基因重組,並且表達出相應的生物學功能,這篇論文宣告基因工程的誕生。
Boyer和Cohen的基因工程技術傳到了資本界,但是大部分投資人偏謹慎,認為這項技術產生利潤至少是十年以後。1976年1月,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撥通了Boyer的電話,他就是投資天才Robert A. Swanson
Boyer起初並沒有在意,只答應給Swanson十分鐘的時間,但這場會議最終遠遠超過十分鐘,兩人足足聊了3個小時,結論非常簡單,創立Genentech,Swanson出任CEO。
Swanson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主修化學和管理,畢業後在紐約城市銀行(現為花旗銀行)工作了四年,隨後跳槽到Kleiner & Perkins做秘書兼會計。當時Kleiner & Perkins剛剛成立,還不是後來享譽全球的凱鵬華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KPCB),當時合夥人也只有兩個。
Swanson大學畢業沒幾年,拿得出手的只有2.6萬美元,只好回去找他前老闆Thomas Perkins要錢。Perkins是KPCB的創始人之一,人稱矽谷之父,最終答應投資10萬美元作為Genentech的啟動資金,獲得Genentech 25%的股份。
Boyer和Genentech通過基因工程技術,1977年用大腸桿菌生產出生長抑素,1978年用大腸桿菌生產出人胰島素。這時候傻瓜都能看出基因工程的巨大應用潛力了。1980年10月,Genentech在NASDAQ上IPO,股價1小時內從$35上漲至$ 88,公司市值達到3億美元。
1982年,Eli Lilly從Genentech引進人胰島素,這款產品即著名的優泌林(HumuIin)。用類似的方法,Genentech做出了一系列蛋白質和單抗,諸如阿替普酶、生長激素、利妥昔單抗、曲妥珠單抗、雷珠單抗等。
1980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Paul Berg、WalterGilbert和Frederick Sanger。Walter Gilbert和Frederick Sanger獲獎是因為發現了基因測序方法,Paul Berg獲獎則是因為首次實現不同種DNA的重組,而首次將基因工程全程走通的Boyer和Cohen與諾獎失之交臂。
2009年,Roche以47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Genentech,這或許是Big Pharma併購潮中最成功的一案。Roche收購Genentech並沒有進行常見的拆分重組,而是保持Genentech獨立運營,為Roche這艘製藥界的航母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中篇
故事開始於2006年,Shinya Yamanaka以逆轉錄酶病毒為載體,將四個轉錄因子(Oct3/4、Sox2、c-Myc、Klf4)導入小鼠的成纖維細胞,成功誘導出乾細胞,即誘導多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Shinya Yamanaka因此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
Shinya Yamanaka的方法是有缺陷的,轉基因過程中可能產生意外突變,這意味著很難實際應用於人體。哈佛大學的年輕科學家Derrick Rossi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他用mRNA代替DNA誘導幹細胞,因為RNA不影響基因組,不會有致癌風險。最終他發明了RNA誘導的多能幹細胞(RNA-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RiPSCs),被評為2010年十大醫學突破。
Rossi有個叫Tim Springer的同事,他既有人脈又有商業頭腦,之前創立了LeukoSite,成功開發出阿崙單抗和硼替佐米,1999年被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 (現屬Takeda)以6.3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Springer把Rossi推薦給了Robert Langer—醫藥界的愛迪生。Langer在43歲時便成為美國科學院、工程院、醫學院三院院士,發表論文數量和專利數量都早已突破1000,他創立了25家生物技術公司,著名的Polaris Venture投資了其中17家。
Langer是很忙的,每天的日程排三頁紙,據說上一趟廁所發7封郵件。有句話說得好,如果你想在波士頓創立生物技術公司,你得去找Bob Langer。在Springer的引薦下,Langer答應給他們2個小時。
真正吸引Langer的並不是Rossi發明的干細胞技術,Langer感興趣的是Rossi怎麼把mRNA弄進細胞,然後表達出相應的蛋白質,這與基因工程有異曲同工之妙。
Rossi並不是第一個把mRNA弄進細胞的人,早在1990年便有科學家曾往小鼠或大鼠體內註射mRNA,雖然產生了少量蛋白質,但效應轉瞬即逝,不適合成藥。外源性RNA會激活天然免疫系統,產生顯著的細胞毒性。細胞正是依靠天然免疫系統,識別外源RNA,從而抵抗RNA病毒的入侵。
Rossi將RNA中的尿嘧啶、胞嘧啶替換為假尿嘧啶、5-甲基胞嘧啶,修飾後的RNA更像是細胞內源性物質,從而克服天然免疫應答(現在用的方法並不是這個,已經發展到第六代)。有意思的是這種RNA修飾方法並不是Rossi首創,真正的發明人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
經Langer點撥後,mRNA技術的前景豁然開朗。3天后,Rossi做了另一場報告,這次他面對的是知名風投Flagship Ventures。
Noubar Afeyan是Flagship Ventures的創始人兼CEO,Genentech成立時他還在上學,幾十年裡他一直在尋找下一個革命性技術。基因療法、反義療法、RNA干擾,一個個被業內稱為”breakthrough”,最終都未能給行業帶來根本性的變革。
Afeyan聽了Rossi的報告後,意見與Langer一樣,幹細胞不算什麼,mRNA表達技術才是天大的機會。
在Flagship Ventures的支持下,Moderna Therapeutics(名字取義Modified RNA)於2011年成立了。之後4年,Moderna風平浪靜,直到2015年1月融資4.5億美元,創造了生物技術融資最高紀錄,銀行存款達到8億美元。2011-2015年間,Moderna通過股權融資了6.25億美元,通過其他非稀釋性途徑獲得了3.25億美元。
除了蜂擁而上的投資人送錢,還有各大跨國製藥集團,AstraZeneca、Merck、Alexion Pharmaceuticals、VertexPharmaceuticals紛紛上門。依托獨特的mRNA技術平台,Moderna建立起自己的生態系統,數十個研究項目全面展開,Onkaido、Elpidera、Valera、Caperna等子公司陸續成立。
Moderna近日開展了新一輪融資,高達6億美元,再次刷新紀錄。Moderna還沒有IPO打算,或許未來還有一輪更大規模的融資。
Moderna目前已經有兩個項目進入臨床研究,其中mRNA 1440是一種mRNA疫苗,已在200多例健康受試者身上測試。2016年7月,AstraZeneca與Moderna Therapeutics在德國遞交AZD8601的臨床申請,這是他們合作開發的第一個項目。AZD8601可在細胞內翻譯成VEGF-A蛋白,從而發揮治療作用。
下篇
Genentech和Moderna的起點都是一篇論文,全球每年發表論文220萬篇,41萬篇來自美國、40萬篇來自中國,從數量上來說,中國已與美國不相上下,中國學者也頻繁現身Nature 、Science、Cell、PNAS等國際知名刊物,但在生物技術行業,將論文轉化為生物技術公司的極少,將論文轉化為技術平台的,我印像裡中國還從來沒有過。
榜樣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或者稱之為思想與文化的傳承。Genentech催生了一大批的風險投資,這些風險投資又將一大片科學家從象牙塔拉進了工廠。Afeyan一天之內決定投資Moderna,果敢堅決,是因為他在求學時代親眼見證了Genentech的騰飛。
“發表論文—成立公司—早期研究—IPO—後期開發—被收購”,Genentech走過的這條路被後來無數的生物技術公司重複。Genentech走通了而且非常成功,後來走這條路的公司有成功也有失敗,但總體看來成功的機率不低,於是許多人都願意踏上這條冒險之路。
社會需要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行業需要一個成功的典範。中國新藥研發史上有兩個影響力極大的新藥,第一個是青蒿素,第二個是埃克替尼。青蒿素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已經不適用於現代,我們總不能開倒車搞舉國體制。
貝達藥業和埃克替尼值得深入討論,作為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中國將貝達藥業樹立為藥物創新的典型。事實上貝達藥業也起到了榜樣的作用,帶領中國數十家製藥公司開發了50多個替尼,如果算上未申報臨床的,這個數字會更加恐怖。影響遠不止如此,你還可以看到數不清的格列汀、格列淨……
埃克替尼是一個典型的me-too藥物,me-too這種研發模式在外國曾經非常火熱,但在高通量篩選技術出來以後,藥物的篩選規模不斷擴大,first-in-class一般就是best-in-class,如果不能研發出me-better,me-too研發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這種模式不像以前那樣受人青睞。
中國製藥公司這兩年應該意識到,貝達的me-too模式是不容易複製的,實際上貝達自己也未能複制出第二個埃克替尼。未來的路仍然是要做創新,而且從頭做創新,做first-in-class,這條路中國沒人走過。
前面討論傳承的力量,而傳承創新的思想終究要靠人才。中國近年通過千人計劃引進了很多人才,研發力量大大加強,但這還遠遠不夠,中國尤其缺一種人才—文武兼備。
在Moderna這個案例中,最初的技術發明人是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他們申請了專利並且創立了RNARx公司,政府給了他們90萬美元的資助(中國也差不多是這種資助水平),但是他們的技術差點被埋沒。
Derrick Rossi本人最初的重心放在幹細胞上,也沒有意識到mRNA技術的重大潛力,但是他足夠幸運,見到了Robert Langer,見到了Noubar Afeyan。Langer和Afeyan都是跨行業天才,一篇普通的論文,經他們腦子一轉,就是天大的商機。
生物技術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一般科學家只能做到精通某一項,會做實驗還會做生意的人才極少。這種人才美國不止一個,至少有兩個,實際上可能成百上千。冒險的精神、創新的文化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
美國的生物技術公司一般都免不了登陸NASDAQ,III期臨床的耗資巨大而且風險不小,IPO後可以籌集足夠多的研發資金,將風險分散給社會,反過來也將創新的收益回饋給社會。
Moderna雖然手上有10億美元的現金,比一般的生物技術公司都有錢,暫時沒有IPO的打算,但終有一天它會去NASDAQ,因為它有數十個項目。如果這十個項目都上III期臨床,10億美元就完全不夠燒。
NASDAQ寬鬆的加入制度為新藥研發提供了資本保障,有效避免了真正有價值的項目因為資金問題夭折。看看中國的貝達藥業,至今還沒有登陸A股,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合適的資本市場來支持新藥研發。
但現階段讓生物技術公司上A股是非常不合適的,中國的資本市場太不成熟,投資者又以散戶為主,難以駕馭高風險的新藥研發。新藥研發的成功與失敗也就是一夜間的事情,弄不好就會把股市變成全民參與的大賭場。
總結來說,美國生物技術繁榮的關鍵在於傳承、人才和資本,其中資本是最容易解決的,只要有錢有製度,總有一天能學會。傳承和人才則是難題,因為能傳承,所以有人才,因為有人才,所以能傳承。
《雪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