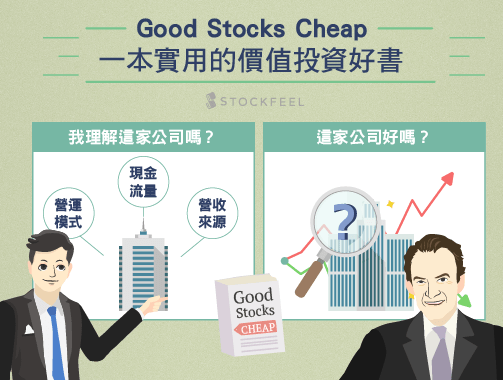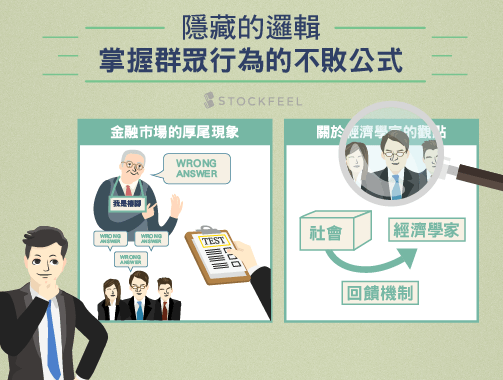前言
- 23 歲獲得博士學位;
- 26 歲成為破譯密碼特工,卻因情商低被解僱;
- 30 歲當上大學數學系帶頭人;
- 37 歲贏得幾何學最高獎項;
- 44 歲闖蕩華爾街,成立傳奇對沖基金公司;
- 56 歲創辦了一系列慈善基金;
- 72 歲入選富比士財富榜全球百大富豪同年書面承諾,將畢生大部分財產捐給慈善事業。
他就是詹姆斯·西蒙斯 (James Simons) ,是世界級的數學家,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對沖基金經理及慷慨的慈善家。在 MIT (麻省理工學院) 的一次演講中,西蒙斯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經歷與感悟。
西蒙斯認為每一件事都有它美的一面,他一生都在“被美麗指引”,找一群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法把事情做正確。
徜徉在數學世界的各個維度,成為數學家
- 年少壯志 – 進 MIT 學數學
這真是一個很長的介紹 (講座開始有 MIT 理學院院長卡斯德及伊斯辛德教授的開場白介紹,本文省略) 。我之前還在擔心我的演講可能太長了,他正好講了一半的時間,所以我能夠專注利用下一半時間,把所有我要講的東西在所允許的時間裡全部傳達出來。
實際上,我真的非常高興能夠站在這裡,我相信我以前曾經在這個教室待過,它看上去很熟悉。除了 MIT ,其他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許多變化。我老是想回到這裡,而且我住在這附近。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總是想來到這裡學習數學,我現在告訴你們我通向 MIT 的有趣之路。
在我 14 歲時候,一個聖誕節前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假期花園的設備供給處,它現在可能還存在。我在一個地下室工作,負責把所有用具放好。我處理得很差勁,我不知道那些東西究竟該放到什麼地方,他們似乎一點規律性都沒有。他們對我的工作很不滿意並且降了我的職務。你們可以通過降職想像他們的情緒 (笑) 。
我被降職去拖地板。我很喜歡這個工作,因為這個很簡單,我不需要動腦子,我可以走動並且思考。走動,思考,而且他們還付我錢。然而聖誕節最終到了,那個工作也該結束了。
這個地下室是由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經營的,他們跟我告別的時候想儘量顯得對我好點,他們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想來 MIT 學數學。他們認為那是他們所聽說過的最最滑稽的一件事了,畢竟我連把東西放在哪裡也記不清。
- 與衛斯理大學失之交臂,最終還是選了 MIT 數學
其實我愚弄了他們,我申請了 MIT ,而且我被錄取了,但後來我接到了衛斯理大學的一個電話 (Wesleyan University) 。我從來就沒聽說過衛斯理大學,我那時只是個高中生,我知道的很少。他們說:“我聽說過你,我們非常希望你能夠申請衛斯理大學。”
我覺得這個聽上去似乎不錯,所以我答應了他們。他們就告訴我需要在週末的時候過來,他們要幫我準備這個準備那個,我要上這個課那個課什麼的,所以我星期五去衛斯理做這些。
不管怎樣,衛斯理是個非常漂亮的地方,自己的好奇心和這個地方的美讓我感到似乎飄飄然了,我申請了衛斯理大學,然而最終我沒被錄取上 (笑) 。最後我沒有任何選擇了,我命中注定要來到這裡 (MIT) 。所以不管怎樣我都來了,我還選了數學,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 影響我職業生涯的數學家和聰明敢闖的大學朋友
我的職業生涯在那裡發生了轉折。我那個時候遇見了 Warren Ambrose,一個非常喜歡啟發人的數學家,可能有一些老員工還記得 Ambrose。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伊斯辛德,不過我還記得在校園角落有個這樣的房間,我知道它在 1971 年就消失了。
那個時候是 1956 年或 1957 年左右,它在早上開放,我們有時候去那兒吃個三明治什麼的。有一天凌晨,Ambrose 突然走了進來,還有辛德也和他在一起,那個時候 Ambrose 差不多 50 歲。他們進來,穿的像個孩子似的,圍著桌子坐下來,忙著討論數學工作。
我想這是世界上最酷的一件事了。這是怎樣的一種愜意的生活呀!就是早上來到這裡,和你的朋友一起一邊喝咖啡一邊研究數學,那個時候可能還會抽幾支菸,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那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我於是追求了這樣一種職業。
是的,我是經常打撲克,除了 Ambrose 和辛德,我還在 MIT 交了另外兩個朋友,是兩個來自英屬哥倫比亞的男孩。當我們畢業的時候,有人曾問過我,我們那個時候是否真的騎著摩托車去了巴西。
其實,那差一點就成了事實,我和哥倫比亞的朋友騎著小型摩托車從波士頓去了波哥大 (哥倫比亞首都),那次旅行我能夠活下來真是個奇蹟!但是我們的確抵達了英屬哥倫比亞,這件事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從來都沒想過我有一天會去加拿大,而現在我居然到了哥倫比亞。
在那個時候,波哥大還是個不發達城市,那個時候你似乎能夠做任何事情,任何的商業都有可能在哥倫比亞變得繁榮起來,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這些商業活動。
另外,這些和我一起在 MIT 讀書的男孩子們是非常聰明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他們經常在玩撲克的時候贏我,他們很可能會成為很成功的商人,而結果也正如我所料,過一會兒我們還會再詳細講這些。
- 商業上小試牛刀
不管怎樣,我畢業之後去柏克萊讀了博士,在那裡我遇到了我的論文導師 Berg Kaster,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然後我回到 MIT 來教書。後來我說服了我的哥倫比亞朋友,我認為他們應該開始做一些生意,因為他們天生就應該幹這一行,而且我之後也會下海。
我後來的確照做了,但是直到我們發現一些其他值得做的生意時我才會離開。那個時候我沒有錢,也沒有名,現在想來可能不行。無論如何,他們不想拋棄我。然而在那兩個星期裡,我們的確找到了一些可以做的生意。我開始做了一個生意並且賺了一些錢,我父親當時也投資了一些錢,那些錢後來為我職業生涯的轉變奠定了基礎。
我在 MIT 教書的時候,我通過借錢對我的生意做投資。幾年過去了,我需要開始還貸,就像所有其他的企業剛剛起步一樣,我們開始期望 18 個月以後就有紅利可分,我們對自己的公司報了太高期望。最終我們是得到了紅利,但是在幾年之後,不過這些紅利數目還是相當可觀的。
- 因不懂人情世故被解僱
我需要還掉一部分債務,所以我去了位於新澤西普林斯頓的美國國防分析學院,那個時候分析學院還是普林斯頓大學校園相連的一個部分,但是他們做的是政府的秘密工作,他們付的工資很高,而且你可以有一半時間做自己的數學研究,另一半時間幫他們做事。那屬於秘密,我不想在這裡討論這些。
他們知道,我也知道。我喜歡這件事,也很喜歡這份工作,況且我做得也不差。我很喜歡設計模型然後把它們寫成程式。當然程式不是我寫的,不知道是他們哪個人寫的,把它們編成程式然後對這些模型進行測試,看看哪些有用哪些沒用。
那時候我的數學研究做得也相當不錯,還獲得了維布倫獎,我解決了一個幾何學上的比較重要的問題,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
然而,那個時候正在進行越南戰爭。這個機構的主席,他的職位在我當地老闆的上面兩級,他寫了一篇關於這次戰爭的很激進的文章,反正我覺得是比較激進的,刊登在了紐約時代的雜誌版上面,說的是我們會怎麼樣贏得這場戰爭,說是勝利已經不遠了,都是這些類似的事情。
我不大同意他的看法,我們做的工作與越南戰爭無關,但是對於我們的頭頭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我覺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後來給紐約時代週刊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的觀點,結果他們發表了,幾個星期後刊登在同樣的週末版上。
於是我被列在了監視名單上,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被列上了監視名單。幾個月後有一個人來找我,他是新聞雜誌的一個報導員,他在寫一篇關於那些在國防分析學院工作但是反對這次戰爭的文章,他正在為找一個合適的人做採訪而發愁,但是他聽說了我。
他讀了我的文章,並且問我他是否可以採訪我。我說當然可以!你們可以看得出我當時是個多麼精通世故的人 (反語) !他問我做什麼工作,我如實回答了他。
我說既然他們說可以允許我一半時間幫他們工作一半時間做我自己的數學研究,那我的原則就是在現在我完全只做我自己的研究,不過我會記錄下我的時間利用情況,等戰爭結束了我會花同樣多的時間去做他們的工作,這就是我的工作方法。我覺得這個回答其實很合理。
後來我回去告訴我當地的老闆,說我接受了這次採訪,我做了一件比較聰明的事,只是有些晚了。
我的老闆問我,你真的接受採訪了?你都說了些什麼?我回答說我說了哪些。他說我最好給 Taylor 打個電話,他拿起了電話打給了總負責人Taylor,但是電話那邊沒有聲音,他沒聽到 Taylor 在說什麼,他掛掉了電話說:“你被解僱了。”“什麼,我被解僱了?”“是的,你被解僱了。”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解僱。我說我是個“永久成員”,那是我的頭銜 (笑) 。他說讓他來告訴我這之間的區別,當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是個“暫時性成員”,但是當我被解僱後,我就會成為一個“永久成員”。“暫時性成員”有個合約 (contract) 。
我想恐怕的確是這樣,當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要簽一份合約,但當我被解僱的時候,我不需要簽什麼合約。所以那是我不太順的一年,但是我並沒有很焦慮。
- 成為石溪大學數學系主任
我的確沒有採取伊斯辛德的意見,我接受了石溪大學提供的職位,我認為成為一個炒別人魷魚的人要比被別人炒魷魚要好。的確,雖然很遺憾,但是那個時候我的確要炒很多人的魷魚。
這個數學系開始很差,但是我們招了很多人,後來我們的確做得很好,我們把它打造成了一個很好的部門,在陳 (陳省身先生) 的幫助下,我在那裡的數學研究成果最後在物理學領域也變得非常有用。
我是在那裡學會了我們數學家所稱的纖維叢連接性和物理中所謂的規範場論之間明顯的關係。於是我回了 MIT ,實際上不是 MIT ,只是在某個咖啡廳裡,把關係解釋給伊斯辛德聽。
那是一次令人激動的討論,可能與大多數在咖啡廳進行的討論一樣,關於物理學的演變,以及它與數學幾何學方面逐漸地互相靠攏。從今天來看,實際上它們真的有極大的共通之處。
數學家的華麗轉身,成為傳奇的量化投資大師
- 從數學家到投資家的轉換
那些的確都是美好的時光,但是正如伊斯辛德所說,後來我的確因為被一個問題困擾而變得比較灰心,我想去證明一些數 — 無理數,我想你們都知道無理數的概念,可能一個數是有理數還是無理數並不是很重要,但是在這個問題當中,這個概念卻有許多其他的意義。
我完全不能夠勝任這個問題。這是個好問題,無理數直到現在仍然是數學界的研究問題之一,至今無人解決。不管怎樣,我變得很氣餒,而且我那個時候作為有過錯的一方正在辦離婚,但是我同時在新的婚姻面前也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和我當時的新女朋友結婚。她現在正坐在台下。
而且我的南美洲的生意也開始分紅了,數目相當可觀,我獲得了一大筆錢。我把那筆錢投資出去,我發現我在投資方面做得並不差。所有的這一切讓我意識到現在是該做一些改變的時候了。
那是在 1976 年,我剛剛 38 歲。我以為我會一輩子都做一個數學家,真的,從 18 歲開始我就這麼認為。我想我花了近 20 年的時間來進行這個遊戲,但後來我還是決定開始轉向做投資。
- 幸運的投資生涯,開頭偏重基本面交易
我從來沒想過要把數學運用到投資當中。當你讀報紙的時候,你認為你自己做得不錯,我們的確做得還不錯。但是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蒐集一些數據,我想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模型化的,就像我們曾經在 IDA (美國國防分析學院) 做的一樣。
所以我從 IDA 找來了全世界最好的模型創建者,Lenny。在 IDA 的時候我們一起構建模型。Lenny 開始和我一起創建模型,但是我卻一直在做交易。Lenny 似乎對建模越來越不感興趣,而是經常會去閲讀一些新聞,那個時候新聞還是一捲一捲的那種,你把它撕開然後讀新聞。
Lenny 並沒有在想怎麼建模而是一直在讀新聞。然後他會形成自己的觀點比如說市場會上漲,市場會下跌之類,都是關於外匯和債券的一些東西。然後我開始發現很多時候他的分析是對的。
我說:“好的,你是用什麼模型?不妨我們用它來賺點錢吧。”我們的回報率很高,從我問“你運用的什麼模型”開始的兩年裡,我們把我們投資者的錢變成了剛開始的 12 倍,那還是扣除了其他費用的。
聽上去我們做得不錯,我們也是極其幸運的,你們看那個上面寫著一個詞就是“幸運”,或者說“好運”,我們當然很多時候是比較幸運,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的運氣也的確很好。
當時在我的腦海裡想的仍然是我可不想只去建模,但是另外其他的人可以專門建模。Jim Max,一個很著名的數學家,離開了石溪大學後加入了我們,他的確建了一些模型。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把基本面交易 (fundamental trading) 、風險投資 (venture capital) 和所有其他的投資方式結合在一起,我們一直在不斷創造出新的更有效的模型。
- 投資轉向完全依賴模型交易,成為模型大師
最終,大概 10 年後我發現,其實如果你做基本面交易,那麼某一天當你醒來時,你可能會發現自己是個天才,你的部位總是朝利於你的方向發展,你覺得自己很聰明,你也會看見自己一夜之間賺很多錢。
然而第二天,所有的部位都朝著不利於你的方向走,你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我們這方面做得還行,只是這種情況好像不應該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 (因為膽顫心驚) 。既然我們會做模型,那就不妨跟著模型走。
所以,1988 年,我決定百分之百地依靠模型交易。而且從那時起,我們一直都這麼做。
一些公司也運用模型,然而它們的宗旨是,他們有一個模型,用這個模型得出的結論給交易員提供參考意見,如果他們贊成這個結論那就照著執行,如果他們不贊成那就不執行。
這不是科學,你不可能模擬出 13 年前當你看見市場行情數據時的那種感覺。而且回溯測試 (Back test)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如果你要是真的靠模型去交易,那就完全遵照模型說的去做,不管你認為那個模型有多聰明或者是多傻,這後來被證實是一個很正確的決定。
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個百分之百依靠電腦模型做交易的公司,做的業務從我前面提到過的外匯、金融工具,逐漸發展到股票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交易的、流動性強的東西。
那個時候,為了得到數據,我們派人去聯準會影印利率的歷史數據,那些數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你也不可能簡單從網上買到。為了得到區域性數據,我們必須要手工蒐集大量數據,我們確實做到了。
逐漸地,我們變得更加聰明了,那些模型也變得越來越有效,我們還招進了越來越多的人,伊斯辛德說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團隊,我認為這不完全正確。從其他方面來講,這個團隊也不差,我們招了很多很聰明及擅長這些工作的人。
我們從 1988 年開始創建大(2106-TW)獎章基金 (Medallion fund) ,1993 年我們不再接受幫外界投資的新業務,只有我們的僱員才能夠投資。2002 年時,我們把所有外界投資業務剝離出 Medallion fund,2005 年時將其買斷 (buyout) 。
從那時起的五年內,Medallion fund 就完全歸我們的職員所擁有,至今大概有 300 名僱員有 Medallion fund 的所有權。
- 成功的秘訣
人們經常問我有什麼秘訣,因為我們不是這世界上唯一一個做量化分析的公司,我們不是唯一一個通過建模來交易的公司,我剛剛批判性地評價了一些運用模型交易的公司。我們公司顯然運行得比其他的公司要更好,我們的確創下了很多交易方面的記錄。
人們總是在問,到底是什麼秘訣?當然是有秘訣的,我當然不會告訴你們各種預測性的參量等等,那些比如說……不,我不會告訴你們的,那是他們研究的東西。
但是,真正的訣竅其實是,我們的起點是一群一流的科學家,他們完成的是一流的工作。因為我們公司一開始就圍繞一些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創建,他們都是經過相應考核的,也一直和公司在一起。
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給我們的員工提供非常好的基礎設施,一直有人告訴我他們從來沒見過一個比在我們公司工作更方便的公司了,那些數據的尋找都異常方便。下面坐著我們的一位校友,我之前剛見過,雖然我不會建議他這麼做,但是如果他想要的話,他可以去試一試我們的系統。
而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保持著一個開放的氛圍,我認為做大規模研究的最好方法就是儘可能地確保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至少是做到越快讓大家知道越好。
有的時候你可能有一個想法想自己保留,但是很快你就覺得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白痴,越快越好,告訴其他人你在幹什麼,因為那樣才能最快地刺激你一些事情,沒有分隔,沒有小集體。比如說,認為是我們幾個人建立的系統,我們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一類的事情決不會發生。
每個星期我們的研究員就會聚一次,討論新的想法,而且最好是能夠運用到實踐當中去的想法。
所以這是一個寬鬆的、開放的環境,你的工資是基於公司整體利潤的,而不是根據你個人自己的工作,每個人的工資都給來自於任何一個其他人的成功。
不過沒有任何一項政策能單獨使效果達到最好,而是需要所有政策都能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出色的員工,很棒的基礎設施,開放的環境,並且儘量讓每個人根據整體的表現獲得薪資。這個方法很有效,而且將一直有效,並且靠著它我們賺了很多錢,足夠多的錢。
成功之後的忙碌 – 慷慨的慈善家
- 創建基金會,支持基礎科學及跨學科研究
之後我們創建了一個基金會,是我的妻子和我在 1994 年創立的,剛開始只是以她的化妝間為辦公室,是嗎? (問台下他的妻子) 有一個小盒子,還有很大的文件夾。
她的化妝間不大,那是個總部,後面逐漸地向外擴展。她先僱了一些人,然後又招了更多的人。因此我們有了一個基金會,而且在很快地擴大,不僅僅是從我們給出的錢的數量上來講,也從機構運作的成熟程度上來講。
這非常好,我的第一份職業是一個數學家,我的第二份職業是成為一個商人,我的第三份職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做一個慈善家。
那我們的基金會都做些什麼呢?
我想我們的基金會是少數幾個幾乎完全對基礎科學做投資的基金會之一。我們支持基礎數學、基礎物理,還有很多生物方面研究,但是最普遍的是一些跨學科的研究。
我們有一個研究自閉症的項目,非常的有意思,它嘗試用電腦從基因方面來分析這種情況,以發現不正常的大腦是怎樣工作的。所以我們主要集中於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瑪麗蓮和我都認為這麼做很好。我們同樣也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其他的事是小規模的。
如果單從對基礎科學的投資規模上講,應該還沒有一個基金的規模能夠與我們相比。首先,我們給相關機構提供錢,我們幫助 MIT 提供資金給數學系的教授做科研。
但是最近幾年我們更加集中於建立數學、物理學和生命科學之間的橋樑,以及事件研究機構等,這些都對我們很重要,自閉症的研究也很重要。現在我們更加注重於數學和物理學研究,關注個人項目。
MIT 在理論電腦科學方面有所實踐,那也是他們唯一的實踐,他們知道我知道這一切。不過這是一個不錯的應用,我承認應該還有其他地方需要這樣的實踐,理論電腦科學也將會拓展到其他方面,這就是我們基金會在做的一些事。
- 創建 Math for America
我 2009 年從基金會退休,但是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忙。人們常說你都退休了,怎麼可能會很忙,但是實際上我真的非常非常忙。為了提高數學教學水平,我們在幾年之前創建了 Math for America。
每個人都很關心美國孩子的數學教育問題。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觀點。我們通常狹義的觀點是,我們的老師懂數學。你會說當然了。但是很讓人吃驚的是,尤其是當你上了中學,你會發現大部分的數學老師數學懂得卻不多。
這不是一個很有效的環境,至少在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科學或者任何其他東西的興趣時表現更加明顯。如果你選了義大利語課,你不想要一個母語是中文的人來教你,你想要一個母語是義大利語的人來教你,雖然他們都能讀義大利文,他會說我學過義大利文,你們不用擔心,但是你卻在想,不,我想要一個母語是義大利語的人來教我,但是實際上孩子們別無選擇。
為什麼我們沒有足夠的教師來教這些孩子們課程呢?為什麼我們沒有足夠的真正懂數學和其他科學的老師來教他們呢?其中一種回答就是如果他們真的懂這門學科,那他們可以帶著同樣多的知識去 Google,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GS-US) (Goldman Sachs) 或者其他地方工作。
因為現在的世界變得更加量化,經濟也比三四十年之前更多地建立在量化的方法上。即使他們適合做老師,但因為存在著薪資水平以及名譽地位的不同,他們也會被其他地方挖走,你很少看見這些人留在課堂上授課。
所以我們必須使這個職位變得更加吸引人,這也就是說給他們發更高的工資,這也正是我們在紐約和幾個其他城市通過我們的項目正在做的,給老師們更多的尊重,並提供更多的支持。
只要我們給他或者她多支付 25% 的薪酬,讓他們感覺到不一樣。一下子,這個職業就變得更加好。如果我們讓這個職業變得更加吸引人了,就會有人追求這個職業。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那情況將會變得很糟糕。所以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考慮的問題。
盡你所能和最優秀的人合作
作為總結,當我告訴我的妻子將會在這次演講中說些什麼的時候,她說,你應該以一些道理來結束你的演講。實際上我沒有什麼道理要告訴你們的。她確信只要我拚命地想,一定能夠想到一些道理。
我想我的確是有一些道理要講,或者說是一些指導性原則而已,“道理”這個詞似乎有點太嚴肅了,但是我會告訴你們一些我自己認為比較好的指導性原則。
有一件我經常做的事就是嘗試一些新的事情。
我經常喜歡嘗試一些新的事情,我不想和大部隊一起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跑得太慢了。如果 N 個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同一時間做同一件事,對於我,我想我會成為最後一個做完事情的人,我絶對不會贏得這場比賽。
但是如果你在同一時間要去想一個新的問題,或者有一種和其他人不同的新的方法,也許那會給你一個機會。所以,嘗試著做一些新的事情。
第二,盡你所能和最優秀的人合作。
當你發現一個很不錯的人,並且能夠與你一起合作做一些不尋常的事,你要嘗試著想辦法一起去做,因為這會擴大你的視野,讓你從中得到一些好處,而且和很棒的人一起工作也很有意思。
我還要說下“被美麗指引”,我認為每一件事都有它美的一面,至少對於我來說是這樣。你可能會問,建一家交易公司有什麼美的一面呢?它美就美在做正確的事,找一群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法把事情做正確。
如果你認為你是第一個這麼做並且做正確的人,我想你就是做對了,這種感覺非常的好,把事情做正確是一件很美的事。同樣,人們沒想過,其實解決數學問題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被美麗指引”是一個很不錯的指導性原則。
然後我還寫了,不要放棄,至少嘗試著不要放棄,有時花很長時間去做一件事是正確的。
最後,讓我們期盼一點點好運。那麼今天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了。
《雪球》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打破CEO神話-四項成功領導者的關鍵特質_-.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