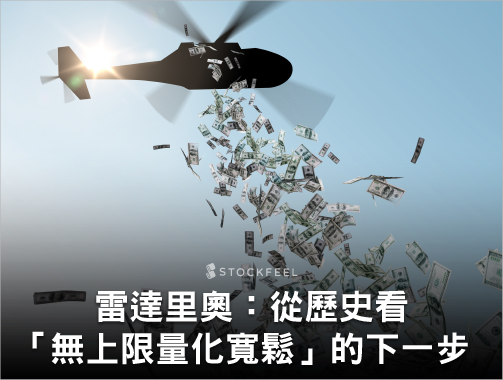無庸置疑地,葛瑞・席林(Gary Shilling)是少數我們應該關注的經濟學家之一。席林一生中所預測成功的事蹟相當令人著迷;他對於現今經濟環境的真知灼見也令人印象深刻。當你遇見席林時,你會感受到他的知識內涵與謙虛的態度。席林總是能為我們帶來啟發。對於尚不了解席林的人,我相當建議你可以閱讀我們去年與他訪談的內容。
- 38年前(1978年)你開設了一間公司,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回想過往,你會做出怎樣不同的決定呢?
我會想早一點成立自己的公司;我一直很希望能夠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公司。因為我的個性比較獨立,不適合為別人工作。我可以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我想這就是自己何以成功的理由。
我發現金融服務業的難處在於許多人都對未來過度樂觀。誠如你所知,我曾因為預測到經濟的衰退,而被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 & Co, MSPX-US)(Merrill Lynch)的執行長Don Regan開除了兩次。我曾是美林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在1968年曾預測1969至1970年所發生的經濟衰退。我認為美國當時的狀況並不樂觀,而這與美林證券當時的口號恰好相反。
也因此,Don Regan把我辭退了,我只好到另一家公司;但這間公司後來卻被美林證券買下,因此我又被辭退了一次。在所有華爾街的故事中,我是第一個被Don Regan辭退兩次的人。實際上,許多人受到華爾街的影響而過度樂觀,然而也不是只有我因為抱持著不同的看法而被辭退。
只要你永遠對於事情保持著樂觀的看法,那麼對與錯並不是那麼地重要。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曾經歷過好幾次的熊市與經濟衰退,但他們卻從未預測到任何一次的危機,甚至他們從未討論過這些議題。再一次強調,如果我可以重新再來一次,那麼我會提早準備、再一次去體驗那些經歷。
- 先前你曾告訴我說,你成功地賭對了澳幣眨值,可以再說明更詳細一些嗎?
在中國成長趨緩的時候,很容易能夠判斷澳幣的走勢。受惠於全球化的影響,許多已開發國家的生產線都轉移到中國,我認為這是過去30年來最重要的全球經濟大事。不過,這現象並沒有改變整體製造業的貨物需求量,而是生產線不斷集中至中國。
澳洲是供應中國煤礦、鐵礦與其它礦產的主要國家。而中國除了控制貨幣外、還控制了股市,基本上你很難放空中國,你只能透過香港的股市來放空中國,但這還是有點不一樣。因此,透過澳幣放空中國是最簡單的方式。澳洲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礦產,它們不斷地挖掘礦產銷售到中國。放空澳幣是相當合理的一件事。
- 在判斷是否有機會放空/作多貨幣的時候,你會依循什麼樣的準則?
我認為貨幣會與全球經濟的成長率連動。每個國家無不尋求提高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方法,如果這無法透過提高內需實現,它們就會設法增加出口。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就是想辦法讓它們的貨幣貶值。因此,全球都想讓它們的貨幣價值低於美元;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澳幣、加拿大的加幣、紐西蘭的紐元等、巴西的雷亞爾與墨西哥的披索一樣。
歐洲和日本的央行刻意讓它們的貨幣貶值。原因無他,它們想藉此提升出口量。你可以稱為這種模式為“模仿經濟學”,包含南韓、台灣與其他的亞洲國家都參與了這個行列。當然,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在一年前就開始讓它們的貨幣貶值,但這對它來說卻是很難達成的。中國股市的崩盤使得巨額資金外流,因此他們想藉由降低外匯存底來調節,外匯存底因而從4兆降到2.2兆元。雖然中國想讓它們的貨幣貶值,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怕如果這麼做,將可能導致更大的資金外流。
而中國所做的應對方法之一,就是將它的貨幣與其它國家的貨幣綁定;所以可以說,它們只不過是跟隨大家的腳步,向其它國家的貨幣看齊而已。然而中國的作為其實相當不透明,並不能確定它們是否真的在與美元對抗。我想,就所有的貨幣而言,美元是最能夠作為賭注的標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想讓它們貨幣的幣值,變得比美元更便宜。
- 當我們在觀察貨幣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評估貿易出口量?
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看,你可能會留意出口量,但我認為出口本身並沒有那麼重要。在進出口平衡的前提下,許多國家僅看重如何增加出口量。雖然出口對貨幣來說是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但我仍無法確定這是否與政府政策同樣的重要。
我認為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加拿大幣、澳幣與紐西蘭元,就是這種商品貨幣的的例子。它們的幣值一直非常的低。就如日圓與歐元的變動主要由央行政策驅動。
- 若想更深入了解貨幣與它們的相關市場,你會推薦那些作者或書籍呢?
就我現在可以想到的,貨幣市場已經與理論上正常的決定因素脫鉤。例如,有一件近期相當受矚目的事情,就是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這指的是大麥克在英國、法國、加拿大與中國等地區的價格都會是相同的。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之下,透過匯率的調整會使各地的貨幣價值差不多;但不幸的是,貨幣是由政治政策所操控的,所以我無法建議任何的書籍。
就貨幣出現以來,它就與全球經濟成長率互相連動;隨著成長的放緩,並且我們現在處於去槓桿化的時代;1980與1990年代所產生過量的債務,讓我們有著極度貶值的需求性。然而,當每個國家的貨幣都在貶值時,這個效益也將會相互抵消。
- 你目前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就政治而言,有許多政治人物日前就相當受到矚目,如: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法國國民陣線-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與英國工黨黨魁- 傑若米‧科賓。德國與法國顯然存在極左與極右派人士,當然美國也是。所以顯然在過去的10年中,歐洲與北美絕大多數人民的薪資在考量通膨之後,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成長的。
群眾對此也逐漸覺醒,他們開始指責檯面上特定的政治人物。就像1976年的電影-《螢光幕後》,裡面有個人大喊著"我就如同將入地獄那般瘋狂,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想這也是許多歐洲與北美選民的心聲。我想,這可能會推動大型的財政刺激政策,因為貨幣政策無法再次收得成效。
在美國,你在兩個領域會發現這樣的情況;第一是基礎建設,我們的確需要許多和舖路、造橋樑與蓋鐵路相關的工作,多數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士必然也深感認同;另一個則是國防支出,如果共和黨能控制參議院與白宮,這情況就會變得更有利;就像你看到日本朝軍國主義之路邁進,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樣。
在這次的選舉當中,我們已經觀察到有些令人挫敗的事跡,我們將會持續觀察事情的演變。像是馬琳·勒龐可能變成法國總統嗎?這是有可能的!當然,美國也對此相當感興趣,我也非常地關注目前的選舉走勢。我認為,即使主流的政治人物當選,也許國會和新總統會想要施行一些經濟刺激的政策,畢竟選民已經非常不開心了。
- 你認為財政政策是件正確且應該做的事情嗎?
美國確實可以透過基礎建設來發展;目前經濟的發展遲緩,絕大部份的勞工市場也處於這樣的情況,產能利用率也不高。因此未來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唯一的問題在於資金是否能被有效的利用,這也牽涉到政府相關計畫;儘管它們釋出了相當大的善意,但相關支出卻沒有顯現出應有的效益。
- 那麼你會如何去改變?
我想,我會很願意投資在基礎設施領域,包含建築公司、原物料供應商與相關的基礎產業;如果投資額更高的話,那麼美國經濟復甦的速度,將會比其它方法來得更快速。若不如此,我們仍需為1980至1990這年代所累積的債務而賣力工作;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去槓桿化的過程將會結束,這可能還將持續好幾年。
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明顯為整體經濟帶來效益。但這也要等選完新的總統與參議院後才會開始;可能還要兩三年的時間才會就緒,但觀察市場對於未來的期待,你將會感受到對未來的預期心理會比實際上的投資進展還要快速。
- 你認為中國最糟糕的時期還沒到來,還是已然過去了?
中國因為全球化而受益,工業生產的步伐也使經濟繁榮。中國已然成為最大、最受矚目的經濟個體,這情況如同早期的澳洲一樣。不過全球化的進程,目前已經走到成熟階段。在1800年代末美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大概約落在50%;20年後,比例已經驟降為20%;而現在也僅剩下12%。我認為,這代表著製造業遷移到中國的趨勢已經結束。
我們已然處在成長率最低的的發展週期上,過往中國高成長率的榮景將不復見。中國能有如此高的成長率,是源自於大量基礎設施的投資,不過這也創造出許多鬼城、過量基礎建設的問題,以及財政上沈重的債務負擔。這段榮景顯然已成為過往。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從出口和基礎建設轉向消費者經濟,但這段轉變過程將花費許多時間,這項轉變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
觀察全球化對世界其它地方的影響,也可看出這股力量的確已經結束了,從進口中國的商品增加,也可得知它們的榮景不再了。這與早期的日本倒是很像。就如每個人所知道的,日本雖然在1980年代在世界上位居要角,但隨著1990年代股市崩盤後,他們也經歷了房市崩盤的危機,在之後整整20年的時間,日本毫無表現。我認為中國將無可避免地面臨類似的危機,而它在世界舞台上所受到的目光,也將隨之而去。
- 經濟學家指出,金融工具使金融業變得更脆弱;過度頻繁的創新,也讓許多金融產品承擔過高的風險,很可能出現不合理的價格,也很難透過現行法令來控管。許多人也因此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對法規作修改。但是,你認為這對於連結緊密、極度複雜的全球金融市場來說,是可能實現的嗎?
毫無疑問地,金融市場目前已經過度超載了。財務的唯一功能,就是提供資金,作為企業的加速器。如果融資過度,將會變得沒有效率。這也是近幾年所發生的事情。隨著經濟成長趨緩,這問題也顯得更加嚴重;金融掌管了一切,同時它將自己逼上了絕路,產生了過度融資的現象,一般來說,唯有金融危機可以抵銷一切。
但實際上並不全然是這樣。特別是在美國,銀行的財政救助使它能夠完好無缺,我不確定法令上的更多限制是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如果增加對銀行的管控,會有許多資金流向影子銀行、對沖基金與私募;我不確定這是否屬於正常的情況,畢竟你無法知道實際的情況、運用槓桿的程度,在這些領域的相關法規並不多。
然而,這樣的情況將會持續發生,政府的紓困方案就是讓這些大型銀行破產,如此才能讓它們的規模縮小到並非不能倒的程度。如果銀行想放棄的話,政府基於效率上的考量必然會說:好,如果你不想破產,那我們就持續地限制你,直到你可能破產為止。
而政府所做的事情就是,限縮銀行自營交易、衍生性金融產品等獲利較高的業務,讓銀行重操借貸業務;從存款來放貸資金,相較於短期的收益來說,長期的收益率曲線是相對平整的,然而,過低的利潤也讓銀行深陷在麻煩之中。監管的結果也影響了銀行未來對資金的需求,我不認為這能讓銀行的風險變成零,而是將風險轉移到其它地方。
- 你會建議增加更嚴格的控管影子銀行嗎?
雖然從理論上也許站得住腳,但如果你這麼做,將會對金融產業與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性,大幅減少金融產業的整體活動,並為經濟帶來相當大的損傷,我想,這是當你試圖控制影子銀行的時候,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 最後,如果我們想度過景氣循環下所產生的金融危機,歷史上有哪些時刻最值得做為我們的省思?
最值得關心的事情在於,我看到人們試圖簡化現行的經濟與金融環境,並視為一個週期固定的循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確實經歷了1950、1960、1970與1980這幾年週期性的景氣循環;然而,金融業的槓桿開始擴張之後,你可以看到,在1980與1990年代,美國金融部門與消費者市場已感受不到任何規則性的景氣狀況,接下來也發生了金融危機、大蕭條與低落的經濟成長率。我認為金融槓桿已創造出迥然不同的環境。
就我的觀察而言,這問題在於人們試圖簡化答案,他們急欲尋找景氣循環模式,並從中判斷我們正處於循環階段的哪個位置上,進而預測下次的循環。我並不認為,目前的景氣循環會像二次大戰後期那樣有跡可循。
我認為許多年輕人都犯了這項極大的錯誤,他們緬懷過去的時代,並認為1950到1960年代的循環週期模型,能作為我們所能依循的劇本,並從中預測未來的走向。我並不認同這樣的想法。我認為,我們正努力解決的龐大金融槓桿、過度膨脹的金融部門,以及全球經濟成長率的減緩等問題,都正是我們過度追求成長下,所衍生出來的罪行。
高經濟成長率的同時,你可能會犯下許多錯誤;但當經濟成長率極低的時候,又很容易陷入蕭條。你可以去看那些非洲的新興經濟體,當商品價格上漲與大量資金湧入的時候,它們並沒有運用這些資金來重建並多元化發展它們的經濟,這也使它們目前的財政狀況陷在泥淖之中。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處在不同的時代,過去的經驗並無法成為現在可行的參考依據。(編譯/Bevis)
《GuruFocus》授權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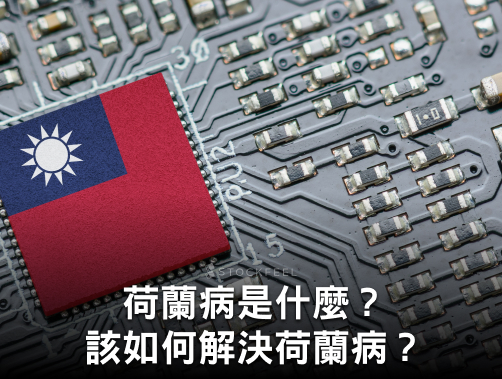








清除絆腳石-_-.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