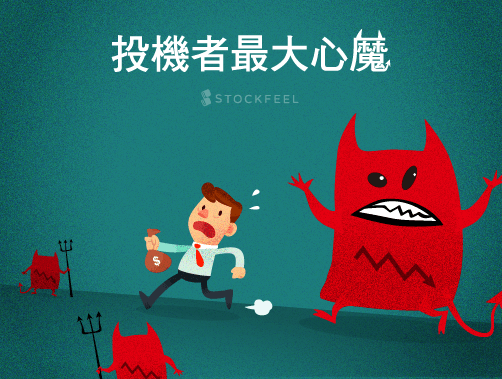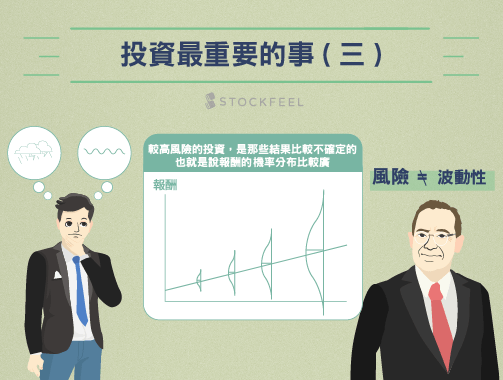在一個暗室裡極難找出一隻黑貓。尤其是在根本沒有貓的情況下。 — 西方古諺語
趁理察·塞勒 (Richard Thaler) 擒獲諾貝爾獎的餘威,我們繼續聊聊行為金融學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你猜,作為一個投資顧問,在給我的那些高淨值客戶交流的過程中,我最常說的三個字是什麼?有問題?您放心?妥妥的?吃了沒?好生意?好公司?好價格?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索羅斯 (George Soros) ?支撐線?您厲害?您賺多少?勿須全程錄音並進行大數據分析我就知道 — 我嘴裡出現頻率最高的三個字肯定是:不知道。
主要是客戶的問題太五花八門了啊,我有時候心裡在想:您這是把我當機器人嗎。揪出幾個典型問題:油價怎麼走?美股什麼時候崩盤?聯準會後面還有什麼招?加泰隆尼亞地區獨立會對歐洲政局產生什麼影響?蘋果(Apple, AAPL-US)公司 (Apple) 的股價是不是到頭了?葛蘭素史克公司 (GSK) 的產品管線到底有多大潛力?
沒有一個不是值 100 萬美元的問題。而我能怎麼答? — 當然是實話實說:不知道。
其實作為一個投顧,在最一開始剛入行的時候我以為我的工作就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絶不虛與委蛇;只要是關於投資,無論是某個晦澀深奧的結構產品 (structured products) ,還是哪個炙手可熱的股票明星,我都要全通全懂,一個堅定的眼神,一個瀟灑的彈指,激盪起客戶對我這個專業人士的深深信任,就是這麼自信。
但在這個行業裡蹉跎久了,就發現這些玩意兒實在不可靠。投資所覆蓋的知識浩瀚星辰,這不是一口又一口的禽糞就能吃出來的,你畢竟生命有限 — 嘆知識太多,但歲月如梭。
比如,有人可能會問我:你覺得雅培公司最新無刺破血糖監測儀 FDA 能批嗎?我能怎麼答,作為一個文科生,對糖尿病我能解釋出個一型和二型的區別就很厲害了好不好;但曾經啊曾經,我是不認輸的,堅決不能向一個完全不懂的問題低頭。
我可能會開始打哈哈:“無刺破啊,什麼意思就是不刺破手指?那肯定是個好東東,你看刺破多疼啊,你不刺破肯定有市場,這利國利民 FDA 肯定得批呀,哈哈哈……”明顯都是沒有訊息量的廢話,現在回想起來我為曾經糊弄過的那些問題汗顏。從沒有訊息量的廢話中,我居然能得出“FDA 會批”這個值千金的結論,這簡直就是犯罪。
當然不是我不願意花時間好好研究一番。但你追所有訊息,就是在追無極。
我們這個時代訊息產生是個什麼速度?據 IBM 的研究 — 早在 2012 年,我們每天產生的訊息就是 2.5 個 quintilllion (100 萬的三次方,或 10 億個 10 億) 位元組。這是什麼概念? — 地球上的沙子總量大約為 7.5 個 quntillion。而我們近兩年內產生出的數據量是已有數據量的 90%。就算是比較難以生產的訊息,訊息中的戰鬥雞 — 科學性學術著作,每十到十二年也要翻一倍。這還僅僅是 2012 年的數據,現在怎麼樣,我都不敢想。
換成現在,不做深入的、且力所能及的研究之前,對任何投資相關的複雜問題,我一概回答不知道。
但你一個投顧怎麼能如此無知呢?你都不知道我們怎麼辦?
先不要慌,半懂是半懂者的催命鼓,無知是無知者的保命符。
無知可怕嗎?也許可怕,至少先人們覺得很可怕,他們戰勝這種恐懼的辦法就是騙自己說天下知識已盡在我手。古人們認為:人類智慧的盡頭都在先哲的書裡,預知大勢你讀個《易經》就夠了,治病救人你讀個《內經》就夠了,如果你讀了並用了卻沒有用,那肯定是你讀得不到位,而不是書寫得不到位。
而另一個極端,是迷信科學是解開一切奧秘之匙。這種信念在近現代尤盛,迷信科學的力量,認為所有的事情只要不斷求索,真相必然自溢,一切的謎題都可被科學所攻陷。曾經很多科學家持這個信念,但現在很多頂級科學家已經沒有那麼樂觀。
曾經大多數科學家堅信“打怪說”,認為做科學研究就是打遊戲,一關又一關地往下打,遊戲是設計的所以總歸是打得出的,打不出的遊戲就是個超級大 BUG。而宇宙之中不可能存在這種 BUG。
在《無知:它如何驅動科學 (Ignorance: How It Drives Science) 》這本書中哥大教授 Stuart Firestein 寫道:“很多科學家認為科學方法就是 ‘觀察—假說—操縱—再觀察—新的假說’ 的無限環形;這種想法不完全錯,但也不全正確,因為這給人一種科學方法是有序過程的錯覺,然而科學方法幾乎從來都不是有序的。”
所以現在興起的理念叫做“暗室說”,比如搞定費馬大定理的數學大天才安德魯·懷爾斯 (Andrew Wiles ) 就說過:“這過程基本就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房間裡亂戳亂撞,最後笨拙地撞到了開關,房內一片光明,然後我們說:哇,原來長這樣。之後我們又進入下一個黑房間。”至於最後撞不撞得開這個開關,甚至到底有沒有開關,我們心裡其實是沒底的。我們應該承認在這個浩瀚的宇宙中有那麼一塊東西,對其我們很可能要永遠地無知下去。
但為什麼人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無知呢?這個可以用行為金融學裡的過度自信偏差 (over-confidence bias) 來解釋。調查研究顯示,大多數司機都覺得自己的駕駛技術在平均水平以上,而大多數經理都覺得自己的公司業績會達到行業平均以上。從邏輯而言顯然很難實現“大多數比平均水平優秀”,所以可以得知作為一個整體,大家都有高估自己的傾向。
順便說一句,這也提醒了我們在做證券分析時,你當然可以搞自下而上的方法 (bottom-up approach) ,採訪公司的員工或者管理層,並拿到第一線的預估分析。但是在數據處理上一定要留個心眼、打個折扣,以沖抵數據向樂觀方向的偏差。
如果我們承認無知,是否就在投資的世界中寸步難行?非也,你可能會百無聊賴,但是你絶對不會寸步難行。
我將無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無可避免的無知 (inevitable ignorance) ,比如明年此時股市點位幾何,這種事你不可能知道;第二種是理性化的無知 (rational ignorance) ,就是追求真相的成本要高於所得收益,那你最理性的選擇可能是保持無知。
比如想要知道秦始皇帝陵博物館裡兵馬俑的準確數量 — 你完全可以買張機票飛趟西安,然後進去一個一個數,最後是能求得真相的。但是你覺得這事費那麼大勁有什麼意義,所以你選擇不去知道。第三種是故意的痴呆 (willful stupidity) ,就是純粹對事實和邏輯漠不關心 — 比如你去重倉一個自己一無所知的股票。
基本上第一種和第二種無知不會傷害你的投資,而第三種危害很大,但卻能夠避免。 這話怎麼說? — 還記耶魯捐基掌門大衛·斯文森 (David Swensen) 告訴你的投資時的三個小夥伴嗎 — 資產配置 (asset allocation) 、證券選擇 (security selection,粗暴點可以理解為選股) 、市場擇時 (market timing) 。其中對於你投資組合的表現,起 90% 以上作用的是資產配置;而我們最為無知的選股和擇時,其實對我們的投資表現起著小作用甚至反作用。這就是說,只要在大方面不痴呆,小方面的無知其實不太傷得了我們。
除了上面說的三種無知以外,還有另一種無知,在投資中危害甚大,叫做知識幻覺 (illusion of knowledge ) ,意思就是你知道得越多反倒錯得越離譜;知道了還不如不知道;我們以為知道,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unknown unknowns) 。
大多數人認為訊息越多越好,訊息越多投資決定越正確,但這是一個幻覺。大量研究能支持這個結論。比如有這麼一個研究,找了兩組 NBA 籃球球迷,兩組對照:第一組給了所有球隊訊息,球隊隊名啊各種數據啊等等;第二組也給了一樣的訊息,唯獨把球隊名字這個訊息隱藏起來。所以第一組拿到的資料上會寫達拉斯小牛隊如何如何,洛杉磯湖人隊如何如何,而第二組的球迷看到的就是 A 隊 B 隊 C 隊的數據。
然後讓球迷們根據所有的訊息去預測之後一百多場的比賽結果。結果令人吃驚,第一組比第二組的預測能力“統計上顯著地”差了一個檔次。而諷刺的是,幾乎所有球迷都認為,如果知道球隊名字會對他們的預測準確率大有裨益,此乃重要訊息。在心理學上這樣的認知會下意識地讓你產生“有把握的滿足感”,進而產生過度自信,對決策帶來傷害。這就是知識幻覺。
某樣東西,我們越熟悉,膽子就越大,幻覺也就可能就越大;但熟悉不代表知識。有這麼一個實驗。實驗者找來三隊人馬一共 100 個人,一隊個人理財顧問、一隊生物學家、和一隊文學系學生。他們都被給出 15 個金融術語 (其中三個術語乃是純粹瞎編 — “預評級證券”,“固定利率扣減款”、“年化信貸”) ,然後向他們逐個詢問是否熟悉這些術語。果然,自認為專家的理財顧問這隊人,明顯更可能說自己熟悉這三個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所以下次你如果遇到你的投顧,可以問問他/她看什麼是“可轉 ETF”,如果其滔滔不絶地給你開講座,那這人知識上的幻覺很大。想不到你濃眉大眼理財師,又來欺騙我的心。
知識幻覺容易導致控制幻覺 (illusion of control) ,讓你有一切盡在我手的錯覺,而這在投資上其實會讓你很破財。康納曼已故的好友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也是紅顏薄命,挺住了就能拿諾貝爾獎) 就發現,人們願意慷慨支付 20% 的溢價去賭一件“熟悉”的事情;而最後卻因為這種自信,他們往往會虧掉這筆錢。
有人可能會問了:你這是什麼意思,反正無知了,那我們投資時是不是不要做功課啦,那我們的勤奮都餵狗啦? — 千萬不要這麼理解,能做的且值得做的功課不做,那就是 willful stupidity。我的意思是熟悉不等於知識,而要把熟悉轉變為知識,還有一個偽價值投資到巴菲特的距離要走。
《雪球》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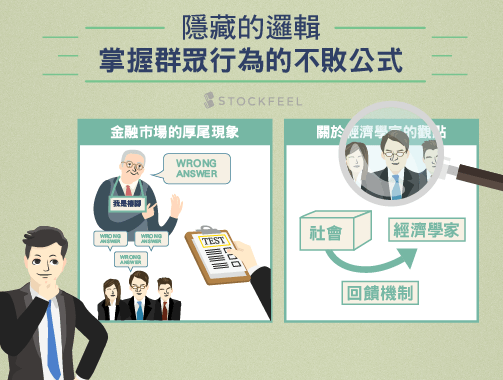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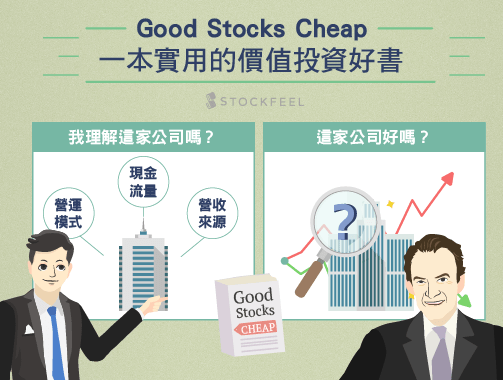




特斯拉與Solar-City間的秘密-華爾街究竟有多醜陋ai.png)